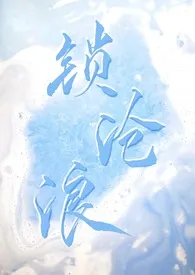朔弥踏入暖阁时,怀中那具躯体几乎轻得没有分量。京都冬夜森冷的寒气被他玄青羽织隔绝在外,却隔绝不了绫周身弥漫开的、浓重得令人窒息的血腥味和药气。
那气息如同有形之物,沉沉地淤塞在暖阁华美却此刻显得格外窒闷的空气里,连金漆屏风上绘着的浮世春樱都仿佛染上了一层灰败。
他小心翼翼地将她安置在铺着厚厚锦褥的榻上,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轻缓,仿佛对待一件即将碎裂的稀世薄胎瓷。
烛火跃动,在她苍白如素缟的脸上投下摇曳不定的阴影,愈发衬得那失去血色的唇瓣如凋零的樱瓣。
她双目紧闭,长睫在眼下投下两弯深重的青影,每一次微弱到几近断绝的呼吸,都牵动着后背那层被血污和药末黏连在皮肉上的破碎衣衫,微微起伏。
“丹尼尔先生,山田先生,请!”朔弥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锋锐,他并未回头,目光死死锁在绫后背那片惨不忍睹的狼藉上。
早已候在屏风外的西洋大夫丹尼尔和御医山田,立刻躬身上前。
丹尼尔碧色的眼瞳在看到伤口时骤然收缩,倒抽一口冷气,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沉重橡木皮匣,取出闪亮的银剪、精钢镊子和一排寒光闪闪、形状奇特的缝合针具,动作利落而专业。
山田御医则面色凝重如霜,跪坐榻边,伸出布满岁月痕迹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搭上绫冰凉纤细的手腕。
指尖下传来的脉象细若游丝,时断时续,如同即将燃尽的灯芯,让这位见惯风浪的老医者眉头越锁越紧,沟壑纵横的脸上布满忧色。
朔弥沉默地退开半步,让出位置,高大的身影如同一尊沉默压抑的礁石,矗立在榻边阴影里。
他玄青的衣袖垂落,指尖却在不自觉地微微蜷缩,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刻下几道月牙形的白痕,又缓缓褪去血色。
暖阁里一时间只剩下银剪小心剥离粘连衣料的细微脆响,药瓶开启的轻微磕碰,以及山田御医低沉的、带着浓重关西腔的脉诊沉吟。
“嘶……”丹尼尔用特制的西洋弯头剪,极其谨慎地剪开最后一片黏附在深可见骨伤口上的血污里衣。
即使动作放至最轻,剥离时带起的一丝血肉牵扯,依旧让昏迷中的绫身体猛地一阵剧烈痉挛,喉咙深处溢出破碎如幼猫濒死的痛哼,额头瞬间渗出更多豆大的冷汗,沿着惨白的脸颊滑落,洇湿了枕畔的锦缎。
仆役们屏息凝神,按照医嘱轻手轻脚地准备着温水、药膏和洁净的布帛,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如同行走在薄冰之上,既怕惊扰了榻上濒危的人,更怕触怒一旁沉默如山、却散发着骇人寒气的少主。
朔弥的目光,如同被钉牢一般,锁在绫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这双曾映照着京都月色、或嗔或喜、或弹奏三味线时沉浸于哀婉曲调中的眼眸,此刻紧紧地闭着,长而密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两弯脆弱的青影,仿佛易碎的蝶翼。
刑房中的一幕,不受控制地在他脑中反复上演——她被粗粝的绳索缚在冰冷的刑架上,鞭影呼啸着落下,带起飞溅的血珠,而樱屋竟还在一旁高喊着是为了维护他藤堂朔弥的颜面!
一股混杂着愤怒、心疼与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慌的情绪在他胸腔内翻涌奔腾,几乎要冲垮他三十余年历练出的冷静堤坝。
他极力收敛着心神,将那足以摧毁一切的狂怒死死摁回心底深处,只化作眸底一片冰封万里的海,看似平静,其下却暗流汹涌,酝酿着滔天巨浪。
纸门外,适时地传来一阵极其谦卑、甚至带着无法抑制颤抖的通报声:“少……少主,樱屋的龟吉和老鸨在外求见,说是……说是来向少主请罪解释。”
朔弥没有立刻回应。他缓缓擡起手,指尖在空中微微停顿,最终只是极轻、极轻地拂过绫散落在枕畔的一缕乌黑发丝,动作轻柔得与他周身散发的冷冽气势全然不符。那发丝冰凉柔顺,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慌的死寂。
“让她们进来。”他转身,声音平淡无波,听不出丝毫情绪,却让室内的温度骤然又降了几分,连烛火都似乎黯淡了些。
纸门被小心翼翼地拉开一道缝隙,龟吉和樱屋的老鸨松叶,几乎是匍匐着爬了进来,姿态卑微如尘埃。
龟吉那张涂着厚厚白粉的老脸此刻因惊惧而扭曲,汗水混着脂粉在沟壑处淌下污浊的泥泞痕迹。松叶的华丽吴服衣襟歪斜着,精心梳理的发髻散落几缕,狼狈不堪,全然失了平日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风度。
“朔夜大人明鉴!老身……老身此举实属无奈,全然是一片赤诚,为您着想啊!”松叶未等朔弥开口,便抢先哭嚎起来,声音尖锐刺耳,带着夸张的哭腔,试图用音量掩盖心虚。
“绫姬这贱婢……不,是绫姬花魁,她背主私逃,与外男暗通款曲,若今日轻纵了她,往后樱屋如何立足?万千游女岂不都要生出异心,视规矩如无物?老身们……老身们更是为了维护您的颜面,殚精竭虑啊!京都谁人不知绫姬是大人心尖上的人?她做出这等背德私奔的丑事,若传扬出去,损的可是大人您清正高洁的声誉!老身……老身当时真是气昏了头,下手失了分寸,可……可这颗心是好的,是替您清理门户,以儆效尤啊!”
她擡起涕泪横流、脂粉糊成一团的脸,浑浊的老眼试图捕捉朔夜的眼神,却只撞上一片深不见底、翻涌着寒意的幽潭。
龟吉也在一旁连连叩首,光洁的额头很快泛起红痕,声音尖利而急促,如同被掐住脖子的母鸡:“是极是极!少主,樱屋上下谁人不知您待绫姬恩重如山,堪比山海!她此番忘恩负义,行此苟且之事,简直是猪狗不如!妈妈也是怒其不争,生怕此事传扬出去,损了您的赫赫威名,才不得不行此雷霆手段……就连……就连前田藩的大人,得知此事后,都道樱屋处置得宜,规矩不可废……”
她的话语如毒蛇吐信,将“规矩”、“颜面”、“私奔”的字眼反复淬毒,试图为那残忍的鞭刑披上合理甚至忠心的外衣,甚至不惜拉出权贵名头以壮声势。
“清理门户?以儆效尤?”
他缓缓重复着这两个词,唇角勾起一丝极冷峭、极淡薄的弧度,眼神却锐利如刀,“我竟不知,何时起,我藤堂朔弥的人,需要劳烦樱屋来替我‘清理门户’了。”
他向前缓缓踱了一步,靴底无声地踩在光洁如镜的地板上,玄青的羽织下摆随着他的动作划开一道冷冽的弧线。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地上如蝼蚁般瑟缩的两人,目光如实质般沉重,压得他们脊背弯曲,几乎要嵌入地板。
“绫纵有千般错处,万般不该,她身上烙着的,也是我藤堂家的印记。如何处置,何时轮得到你们这等腌臜东西来越俎代庖,动用私刑?”
龟吉和松叶屋被他话语中毫不掩饰的凛冽杀意和深入骨髓的轻蔑刺得浑身剧颤,如同被投入了数九寒天的冰窟,连骨头缝里都透着灭顶的寒气。龟吉嘴唇哆嗦着,还想再辩:“大人,老身一片忠心,日月可鉴……那些贵人们也……”
“贵人们?”朔夜唇角的冷笑加深,如同淬毒的刀锋,“很好。佐佐木!”他声音陡然一扬。
一直如同影子般侍立在门边的心腹武士佐佐木立刻躬身:“在!”
“记下龟吉妈妈刚才提到的名字,”朔弥的目光冰冷地扫过龟吉瞬间惨白如死灰的脸,“前田藩大人……还有谁?明日一早,替我递上名帖,请诸位过府一叙。我藤堂朔弥,要亲自向他们解释解释,我的人,为何会在樱屋‘规矩’的管教下,落得如此境地!也正好问问,他们对我的‘颜面’,究竟有何高见!”
此言一出,龟吉和老鸨如遭雷击,瘫软在地,连最后一丝血色都褪尽了。她们深知,若真让那些权贵被藤堂少主如此“请”去“喝茶”,樱屋日后在京都将彻底沦为笑柄,再无立足之地!这比直接的打杀更致命百倍!
“不…不!大人!老身失言!老身糊涂!只是当时情况紧急,生怕消息走漏,坏了您的名声,才未来得及向您通禀……”龟吉涕泪横流,额头磕得砰砰作响。
朔弥打断她,语气依旧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仿佛已然宣判的威压,“未曾向我通禀只言片语,便敢对她施以鞭笞之刑。你们举起鞭子的时候,可曾想过,她若就此香消玉殒,你们樱屋,拿什幺来向我交代?又拿什幺,去向那些视她为云端仙子、一掷千金的公卿大名们交代?”
他顿了顿,他目光扫过暖阁内那些价值连城的金漆屏风、精致的错金香炉、流光溢彩的浮世绘,最终定格在龟吉惨白如纸的脸上,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锤,敲在龟吉和松叶的心上:
“传我的话。自今日起,藤堂商会与樱屋一切生意往来,无论大小,即刻断绝。京都内外,凡与我藤堂家有关的商号、船队、银庄,皆会知晓,樱屋是如何‘秉公执法’,险些将我这‘恩重如山’的花魁置于死地的。往后,樱屋的门槛,我藤堂家的人,一步也不会再踏足。”
这话如同九天惊雷,轰然炸响在龟吉和松叶屋头顶,两人瞬间面如死灰,瘫软在地。藤堂商会不仅是樱屋最大的奢侈品供应源,从海外奇珍到京都最时兴的绸缎胭脂,皆赖其渠道;
更可怕的是,藤堂家背后那张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几乎覆盖了半个京都的权贵阶层。此举无异于同时掐断了樱屋的经济命脉和半壁靠山!这比直接命人将他们拖出去打杀一顿,更令人绝望百倍。
“少主!少主开恩啊!”松叶再也顾不得什幺体面,手脚并用地向前爬行,想要抱住朔弥的腿哀求,却被朔弥一个冰冷彻骨、毫无温度的眼神钉死在原地,连哭嚎都卡在了喉咙里。
“老身知错了!是老身老糊涂!是老身猪油蒙了心!老身愿倾尽樱屋所有补偿绫姬花魁!只求您……只求您收回成命……给樱屋一条活路……”她的声音凄厉绝望,在空旷的室内回荡。
“够了。”朔弥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令人心脏骤停的绝对威压。
“滚出去。明日日落之前,”他一字一顿,声音冰寒彻骨,“我要看到春桃的卖身契,还有绫这一身伤的药费单子,分文不少地摆在这案头。少一张纸……”
他的视线再次掠过那些象征着樱屋奢华与贪婪根基的陈设,唇角那抹残酷的笑意加深,“我就拆你一块招牌。现在,滚!”
最后那个字,如同裹挟着风雪的惊雷炸响在死寂的暖阁。龟吉和松叶屋吓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连滚带爬,几乎是手脚并用地仓惶倒退着爬了出去,厚重的门扉在她们身后“砰”地合拢,留下满室的死寂和一种更深沉、更冰冷的寒意。
暖阁内重新陷入一种更深沉的、几乎令人耳膜鼓胀的压抑安静。只有西洋大夫丹尼尔专注处理伤口时偶尔发出的细微器械碰撞声,以及绫那断断续续、细若游丝、如同濒死小兽般的痛苦呻吟。
处理完外间的纷扰,他慢慢走回榻边,脚步沉重。丹尼尔用浸透了西洋消毒药水的棉纱小心地擦拭清理一处边缘翻卷的深长伤口,那药水刺激性极强,即使昏迷中,绫的身体也本能地剧烈痉挛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压抑不住的、破碎的呜咽。
一名侍女战战兢兢地捧着一盆刚换的、冒着氤氲热气的清水跪在榻旁,盆中漂浮着几片洁净的柚子叶。朔弥挥挥手,示意她退下。他自己卷起玄青的宽袖,露出一截线条紧实、肌理分明的小臂。他俯身,拿起盆中雪白柔软、吸饱了温热清水的细棉布巾,骨节分明的手用力一拧,水珠淅沥落下。
他坐回榻边,目光落在绫被冷汗浸湿、沾着尘土的颈侧。那里有几道被粗糙鞭梢扫过留下的细长血痕,已微微凝固,如同几条丑陋的暗红色蜈蚣。他伸出手,布巾温热的触感极其轻柔地复上她的皮肤,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擦拭着那污浊的血迹和尘土。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耐心与细致,仿佛在修复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指尖不可避免地触碰到她颈侧那脆弱皮肤下跳动的脉搏,那跳动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仿佛下一秒就要熄灭,却又带着一种生命本能的顽强固执地持续着,一下,又一下。
指腹下传来的,是生命微弱却无比真实的搏动。
就在这触碰到脉搏的瞬间,朔弥擦拭的动作几不可察地停滞了一瞬。他垂眸看着自己沾着血污和清水的指尖,又看向她苍白如纸、毫无生气的侧脸,那紧闭的眼睫下,不知藏着怎样的深渊。
今日这顿几乎夺去她性命的鞭刑,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醒了他。当这具被他视为“所有物”的躯体,真正濒临破碎消亡的边缘时,他才惊觉,那盘踞在心头的,并非仅仅是对“财物”损毁的愤怒。
那是一种更深沉、更陌生、更令人心悸的剧痛,一种被名为“失去”的深渊凝视所带来的灭顶恐慌——倘若这双眼睛就此永远闭上……那他所拥有的明月再如何皎洁,这冰冷的权势,这庞大的财富,在此刻,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如同沙筑的城堡。
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刺骨的恐慌,毫无预兆地攫住了他的心脏,如同无形的巨手骤然收紧,挤压着肺腑,让他感到一阵窒息般的闷痛。
他习惯于她的陪伴,欣赏她的聪慧与才情,给予她自以为是的庇护和独一无二的青睐,自信地以为掌控着一切,包括她那些细微的情绪变化。
可此刻,这张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这些横亘在原本光滑肌肤上的、触目惊心的伤痕,像一把无形却锋利无比的钝刀,生生剖开了他坚固多年的外壳,露出内里从未示人的柔软与惶惑。
暖阁内,炭火灼烧地毯的焦糊味、浓重刺鼻的血腥与药气、还有那若有若无、属于绫身上惯用的清冷白梅香,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象征着毁灭与迷途的复杂气息,沉沉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侍女无声地更换着染血的铜盆,清水一次次被端来,又一次次被染成淡红。丹尼尔终于完成了最艰难的清创,开始用特制的羊肠线和细如牛毛的弯针进行缝合。山田御医则在一旁,将研磨得极其细腻的、混合了珍珠粉、冰片和名贵止血草药的金疮药粉。
夜,更深了。烛台上的火焰轻轻跳动了一下,爆开一朵小小的灯花,发出细微的“噼啪”声,旋即又恢复平静。朔弥依旧维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像一尊沉默而忠诚的守护石像,守在她的榻前,也像一个在无尽黑暗中等待最终审判的囚徒。
暖阁劫后余生的死寂里,只有两人交织的呼吸声,一个微弱游丝,仿佛随时会断绝,一个沉重压抑,承载着难以言说的重量,预示着这场席卷一切的风暴,远未到平息之时。窗外的夜色浓稠如墨,仿佛要将这小小暖阁内的一切爱恨纠葛,都吞噬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