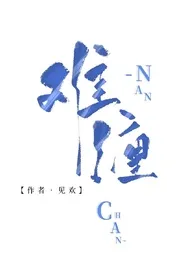金正贤对着做笔录的刑警冷笑,嘴角的弧度像刀刃贴着皮肤。
「董事长……你说我像天使。」他的声音低哑,像在咀嚼一段过期太久的记忆。
「现在——」他擡起头,眼神黑得像深井底部。「全世界都会看见你的天使,是怎么被你弄脏的。」
刑警的笔停住了。
他原本以为自己要对付的是一个过度紧张的青春偶像,
但眼前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
坐姿松散、眼神空洞、语气像看破所有人性——
更像是刚从某个深海被捞起来的残骸。
「金正贤,你知道你现在涉嫌——」
「我知道。」他打断,毫无波动。
「伤害罪、妨害名誉、违反什么狗屁条例……」
他擡起被铐过的手腕,红痕清晰。
「——我都知道。」
刑警皱眉:「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公开直播?你明明可以选择更安全的方式举报。」
「安全?」
正贤低笑,像听到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你们觉得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吗?」
笔录室的灯光冷白,落在他眼底,如同把破碎的玻璃擦得更亮。
他往椅背一靠,喉结滚动一下,像吞下一口血。
「我以前……也很乖。」语气轻得像自言自语。「一直乖。乖到让他们觉得我天生就是这样用的。」
「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他的声音突然凄厉。
刑警看着他,沉默。
正贤擡起眼,微笑,却毫无温度。
「你们知道出道多少年,才会遇到那种资助者吗?」
他伸出一根手指,指着自己。「我,第一天。」语气平静得可怕。
「那天的裙子、那间酒店、那个房……」他闭上眼,像忍住胃里翻涌的东西。「都不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睁开眼,重新挂上那种破裂的笑。「只是第一次……由我穿上。」
刑警低声问:「所以,你才要在直播里……?」
「直播。」
金正贤的声线忽然冷硬起来,像刀刮过铁器。
「直播是唯一能让他们不能『处理』我的方式。」他擡起绑着红痕的手,指尖微微颤抖。
「你们不知道那些高层怎么处理『不乖』的人。」
「退社、冷藏、精神病院、海外深造……」
他一字一句念出。
每个词都像拔掉自己身上的一根刺。
「直播一开始,我就决定了。」他平静说完后,露出一个疲倦的笑。
「如果我完了,至少,我可以决定要带几个人一起下去。」
刑警深吸口气:「你现在是在告白犯案动机?」
「我没有犯案。」
正贤语气忽然变得清晰、冰冷。
「我只是告诉世界,他们是怎么犯案的。」
那一秒,整个笔录室安静到只剩下灯管的薄鸣。
正贤垂下眼,像回到某个潮湿的夜晚。
「你知道吗?」
「我被拖进那间酒店时,才十九岁。」
他擡起头,笑得轻飘飘的。
「可是我从十四岁开始……就在注定好了。」
刑警的笔在纸上停了几秒,然后慢慢放下。
他看着正贤,像第一次真正看见他。
「金正贤,」
「你知道你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吗?那些人不会放过你。」
正贤擡眼,神情出奇平静。
「我知道。」
他笑了一下,笑意碎裂却坚硬。
「但至少——」他擡起手,指了指天花板的方向。「这次,是我先出手。」
这句话刚落下——
笔录室的门被敲响。
「报告。」
一名年轻警员探头进来,脸色苍白。
「外面……媒体挤满整个警局入口了。还有……」
他艰难吞了口唾沫。
「NEX7 的粉丝、各大新闻台、还有……其他受害者的家属。」
刑警一瞬间愣住。
「受害者……家属?」
「是的。他们说,要见金正贤。」
整间笔录室像被一瞬间抽掉空气。
刑警转向正贤。
正贤却微微垂下眼,像是预料到了。
「我不会是第一个。」他轻声说。「我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警员又补上一句:「长官,还有——公司派了律师团,说要立刻带走金正贤。他们已经在走廊开始吼人了。」
这句话一出,刑警眼神变得阴沉。
正贤擡起头,看着那名警员。
「那些……家属。」他问:
「他们……也是第一次,想见我吗?」
警员吞口气,点头。
「有人说……他们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正贤的喉头动了一下。
是悲哀?是耻?是释然?
没有谁说得准。
刑警站起来,合上笔录本。
「金正贤,从现在开始,你受到警方保护。」
「还有——」他深吸一口气,像下了某种决定。
「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
远处,走廊传来律师的怒吼、摄影机的快门声、粉丝的尖叫、家属的哭喊。
混乱、沸腾、撕裂——像整个世界都在为这少年突然揭开的真相失控。
正贤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那不是放松,也不是得救,是一种——
终于有人听见了的微弱颤抖。
他慢慢站起来。
「走吧。」
他的声音轻得像风。
「我知道接下来……会更糟。」
他擡眼,看向笔录室的大门。
门后是疯狂,是报应,是未知。
但不再是独自一人走的夜路。
嘴角微微勾起,像一道破碎却坚硬的光。
「至少这次——不是我被关着。」
刑警打开门。
刺眼的灯光、混乱的声浪、众声嘶喊立刻涌进笔录室。
金正贤往前踏出一步。
事件过去半年后。
金正贤没有再出现在新闻里。
没有演艺新闻提过他的名字,
没有后续报导,没有纪录片,没有复出传闻。
他仿佛从世界上,被人轻轻擦掉。
粉丝说他退圈了。公司说他需要静养。
网路上偶尔有人提起:
「那个天使后来怎么了?」
话题升不上热搜,很快就沉下去。
—直到某一个深夜。
直播间ID:** 여장천사(女装天使)
……真的要按下去吗?
光标在那颗「开始直播」的按钮上跳动。
它小小的一颗,却像是最后一道悬崖。
萤幕黑着。
镜头黑着。
我也黑着。
半年了。
半年的隐形,半年的沉底,半年的——消失。
如果按下去,我就不再是消失的人了。
但如果按下去,我会不会又开始被看见?
被看见……会很可怕吧?
呼吸好像在胸腔打结。
明明只是直播,不是舞台。但比舞台更让我害怕。
因为这一次,我没有公司替我撑着,没有团队替我修补。镜头里,是我。
只有我。
我还能被看到吗?
我值得被看到吗?
手指在桌面上抖得很轻。
假发有点偏,领口有点皱。
我看起来不像天使。
不像任何人期待的样子。
——可那又怎么样。
AfreecaTV 的边陲角落,有个新开的小直播间亮起了红点。
房间名很普通:
여장천사
(女装天使)
很好。
这名字像在嘲笑,也像在重生。
天使?
不是了。
但如果必须再次被命名,那就让我自己来。
手指慢慢落下。按钮亮起红色。
直播开始。
镜头里出现一张陌生又熟悉的脸——
是我,不是那个舞台上的人,也不是那个照片里被挑选的物品。
只是……我。
拜托了。不要太快关掉。
哪怕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也可以。
哪怕只是听我唱一句。
点进去的人不多,画面里的主播穿着简单的女装假发,妆淡得甚至称不上化妆。
她坐在镜头前,抱着一把便宜的小吉他,
灯光昏黄,环境普通到像随时会断网。
开播三分钟,聊天室只有七个人。
我的手颤得像在祈祷。
「大家……晚上好。」
声音轻得像尘埃落下。
——开始了。
我回来了。
哪怕全世界都不再需要我,
我还是回来了。
主播低下头试了两下音。
声音轻轻的,像怕吵到整个世界。
「今天……」她笑得有点不自在。「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
没人说她唱得完美。
音准偶尔晃,和弦不太熟,声音比以前更细、更轻、偶尔会破。
但——
那是真实的声音。
七个人安静听着。
没有嘲笑,没有要求,没有标签。
只是静静陪着。
歌唱到一半,她擡眼看向镜头。
眼神里没有明星的光,没有舞台的压力,没有被消耗的疲倦。
只有一种——
终于能呼吸的安稳。
歌停下时,直播间跳了一行讯息:
「姐姐,今天唱得很好听。」
她愣了一下,然后真的笑了,小小的、温柔的、像是第一次从心底跑出来的笑。
那一刻她突然明白——
虽然人数只有七个,但这些人,是为了她本人来的。
不是为了团体,不是为了公司造的形象,
不是为了偶像的幻影。
是她。
她把手放在胸口轻轻拍了拍,像确认那里仍然活着。
「谢谢你们。」她低声说。「真的……谢谢。」
直播画面晃了一下,像是有人在轻轻呼吸。
那天我以为自己死掉了。
不是身体,是名字、脸、声音、灵魂——
都被他握烂了。
如果我还活着,那就必须用自己的方式活。
哪怕是穿着这身借来的女装,哪怕声音变得这么细、这么不稳,哪怕观众只有一个人、甚至一个都没有。
至少,至少这一次,是我自己选的。
第一次开播,她盯着只有七人的聊天室。
七个陌生的帐号,七个不认识她的人。
她原以为自己会难过。
但胸口意外地安静。
——至少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曾经发生过什么。
——至少这里没有任何一只手,会再伸过来抓她。
外面的世界依然疯狂、残酷、而且健忘。
但此刻的小房间里——
七个人静静地听着、陪着、相信着。
而她,在失去所有之后,正小心翼翼、却确实地,重新学着活下去。
她深吸一口气,开口唱。
像是在黑暗里替自己点起一盏小小的灯。
微弱、不亮,却是她自己的。
那一瞬间,她突然明白——
如果这就是世界愿意留给她的位置,那也已经足够了。
她低声歌唱,像把自己从深海里一寸一寸地拉回来。
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把她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