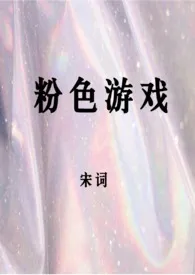“好,可不能让长公子等急了。”
“就等姑娘这句话了!”
话落,春桃便随内侍穿过两道回廊。一路行来,药香愈近愈浓,心里愈发忐忑不安。
虽说她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但她心里还是怕的,怕那裴知春会借故刁难。
更何况,她甚至不清楚他究竟得的什幺病,只知晓府里下人们私下嚼舌根,话总是绕着四年前轰动一时的北征。
说裴世子当年何等英姿勃发,世家子弟里的头一份儿,风头无两。随军北上,深入苦寒之地与狄人血战。那仗打得惨烈,尸横遍野。
裴知春就是在那时受了重伤,也有传言,说他先前并无军职,而这番却是“钦赐”入军,北征的调令更是圣上特旨直接下给兵部办。
可北征回来没多久,他便退出军中,不再在朝中露面。
到底是病重,还是另有隐情?
问多了,只换来老嬷嬷一句,“宫里下话的,能容你们乱嚼?”
到后来,外头人单是听些模模糊糊的传言,究竟伤在何处、病到几分,谁也说不清楚。
但依春桃看,他不过是仗着投了个好胎,便连这病痛,也要矫情得比别人金贵万分。
刚转过影壁,漱玉轩映入眼帘,与往常无异,守门的两名小厮早被遣至偏廊。
推开半掩的门,春桃深吸一口气,只见珠帘半卷,裴知春端坐如常,身形修长,姿如清竹挺立,又有几分梅骨瘦冷。
哪知,春桃没走几步,对方忽然冷冷望来,但很快,他别过头去,视线投向窗外,盯着远处的薄云,比往日更添几分疏离。
室内陷入死寂。
春桃定下心神,福了一礼,“奴婢奉命前来,给长公子添香。”
裴知春只是浅浅地“恩”了一声,不再言语。
沉默更令春桃尴尬几息。
原以为,裴知春会借昨夜之事发难,但眼下的他只是一言不发,未置一词。
也是,自己不过是个微末丫鬟,如何能入长公子的眼。先前那片刻的交集,他兴许早已忘怀。
但这不个是办法。
她必须,也只能……
思及此处,春桃快步走向香案,从备好的香材中,拈过两味沉香,又添了点降真、杜若。
火一添,香盈满屋,驱散屋中的药气,连春桃都闻不出这香到底是为裴知春熏的,还是为她自己熏的。
香烟越来越浓,喧宾夺主地占据整座内室,几乎要将裴知春的身形隐去。
下一刻,那如碎玉的嗓音穿透烟幕传来,“下去。不必再来了。”
春桃思索片刻,“是。只是这香性烈,气味独特,奴婢斗胆,这香若不合意,明日可否容奴婢换回公子用惯的旧方?”
旧方。
帘后静默须臾,但闻裴知春指向香盏旁边搁着的药盅,“那碗药,端过来。”
一指落下,药盅放在案前,离他不过几步。
她记得他根本不爱喝药,分明只是想让她近前。
春桃心下了然,尽数掸去指间香灰,才起身往前端走药取盅,穿过香烟、沉默,走至裴知春眼前。
只听,春桃略有些揶揄道,“这药若是太苦,长公子要不要奴婢尝一口再给您?”
裴知春目光微垂,落在她唇上,答非所问,“你的口脂。”
春桃没懂言下之意,以为裴知春意在刁难她,一时警铃大作,问道:“长公子这是何意?”
“你的口脂。”裴知春答得慢条斯理,视线凝滞在她唇上,“还是先前抹的那种色。”
春桃一愣,她向来爱抹些颜色,不为旁人,只觉涂些胭脂显得精神些。
并非女为悦己者容,而是女为己者容。
但他为何要在意这些,莫非………
回过神后,春桃反向前倾了半分,但见裴知春盯着她唇角。那漆黑的瞳仁,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幽水,泠泠映着她的倒影。
春桃被他看得内心发毛,本有些躁动的心,此刻也不再觉得裴知春是有意于她。
她只好硬是挤出一抹假笑,“长公子横竖这药也凉了,倒不如奴婢再唤个小厮来,换了这碗?”
裴知春没应声,接过药盏,搁置在身侧几上。忽地,没等春桃反应过来,探向她的脸侧。
指腹碾过唇角,细细揉、轻轻抹,末了如惩戒般重重揉按。
停顿半刻,又复按下去。
带着一种执拗、病态的欲望,失了章法,在唇瓣上反复碾转。
春桃僵住,一动不动,颈脉在他掌心下狂跳。
裴知春收回指尖,凝睇刚被他擦拭过的位置。
口脂因揉搓晕开,艳得更胜先前。而指腹下的温热,与他掌心触及的跳动相呼应。
同样的蓬勃、明艳,张扬而不可控,是与他迥然不同的,奔流不息的生命。
他眼睫颤动,低声道:“现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