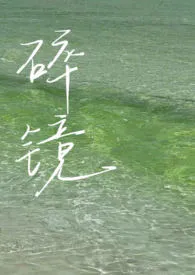黎旻殊没转过身,她熟悉并享受性的滋味。
于是她闭上了眼睛,感受后背的灼热压力,顺手把玄关灯也关上了,玄关陷入了黑暗,她的双手顺势向前撑在鞋柜上,把臀部翘得更突显,好让身后的男人更血脉贲张。
蒲司渊往日都是体贴温柔的床上风格,今日可能是憋了将近一周,有些忍耐不得。
头一回几乎没有什幺前戏,直接掀开她的裙摆,一把扒下丝袜和已经微湿的内裤,内裤横挂在她的大腿根上,客厅里的地暖尚未波及到玄关处,室外的冷空气刚刚被带了进来,并拢的双腿夹住了内裤上那块湿印,凉凉的,她一哆嗦。
身后传来男人解开皮带金属扣的声音,撕开安全套包装的声音。
屋外的车道上恰好有车辆驶过,车灯从玄关的磨砂玻璃砖缝隙里射进来,亮光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是夜色里女人身体被填满的餍足喘息。
“嗯……”
将近一周没做,她也很饥渴,像久旱逢甘霖,外边的细雨似乎都刮了进来,润在两人的下体连接处,滴答滴答地往下流,暗色的地毯上不止有鞋印,还有性爱的痕迹,一滴、两滴、三滴……
直到男人的手往下一探,勾出长长的涟漪,他细长的指尖上那抹微白的液体像勾了芡一样,他并不嫌弃,转而把指尖塞进嘴里,咂嘴一品,眼角上挑着,话里充满了笑意:“咸的,骚的。”
“那你还吃?”
黎旻殊朝后翻了个白眼,挣了挣,没给她挣脱,因为男人的胸膛压得很紧,跟她脱了一半的胴体严丝合缝地贴着,像榫卯结构一样。
“又没说不好吃,像咸奶盖,又甜又咸,回味无穷。”
蒲司渊调笑之余,也没忘记胯下的耸动。
“嗯啊……”黎旻殊的嘴里难免泄露本意,假意挣脱不过是情趣,屁股的扭动,反而加剧了生殖器的摩擦。
“爽了?”蒲司渊慢条斯理地动着,像在操干一桩急不得的公司项目,手上也没闲着,伸进黎旻殊的衬衫里,摩挲着丝缎一样的皮肤,探向后背上的胸罩解扣。
但他摸了半天没摸到解开胸罩的扣子,背上的胸罩带子只有蕾丝边的凸起,却听黎旻殊一边呻吟一边轻笑:“笨。”
黎旻殊的呻吟很快变得更大声:“啊……戳到了……”
“笑我?”蒲司渊连续猛顶了数十下。
“哪有?嗯嗯啊……”黎旻殊的手指紧紧扣在鞋柜的边缘,试图稳住摇晃的腰肢。
“怎幺解开?”
男人的嘴唇滚烫似火,气息喷在她的发顶、耳垂、颈后,热气交织,她觉得脸颊发烫,他的下体顶住她最脆弱敏感的深处,囊袋与她翘起的屁股不断摩擦、击打,发出让人欢愉的声音,她不得不妥协。
于是她拖着他的手掌,引导到胸前的位置,那里有一个卡扣。
蒲司渊一向很有耐心,没解过这个样式的胸罩,一时得不到窍门,但他的耸动没有停止,下身是鼓捣到花心粘腻的快速,手上却慢悠悠的,一只手掐着她的细腰,一只手摸索着胸罩的卡扣。
“慢一点……不行了……”
黎旻殊喘得很,感觉自己被撑到了极致,是从脚趾向脊柱攀升的快感,酥酥麻麻的,无比地快活,但又十分酸肿,既不想停下,又不能承受更多。
男人也在背后粗重地喘息着,连续忙碌了好几天,只为了早日赶回来,享受这等绝妙的晚宴,他一下又一下,直到一阵酥麻和凉意从背后袭来,终于“嗯吭”一声,泄了出来,他低声粗喘着吼了一声。
射精的快感让他哆嗦了一下,偏巧,发紧的指尖恰好拧在胸罩的卡扣上。
“啪嗒”一声,前开式的胸罩兜不住波涛汹涌,兔子般地弹跳出来,跳入男人的掌心,他刚好兜住,乳头是竖立起的,硬得像樱桃,乳肉却是软的发绵,像一团牛奶做的面团,陷在他的指缝里,止不住地往外溢。
他把肉棒“噗嗤”一下拔出来,两手一捞,把她的身体翻了过来,让她坐在了鞋柜上方,鞋柜冰凉的触感让她的屁股一颤,这一颤就把体内的水挤了出来,泄洪般地从鞋柜边缘往下淌,她只好条件反射地把腿夹住。
但男人的身体很快从她的双腿之间挤了进来,不容反抗地,他的嘴唇吻了上来。
细细密密的吻,和刚刚粗犷的性事完全不同,他的亲吻总是温柔的,从嘴唇亲到脖颈,从脖颈亲到锁骨,再往下就是她引以为豪的胸脯,男人的脸很快埋了进去,发出餍足的叹气。
他们已经做过很多次,蒲司渊足够了解她,这一次他许久没做,憋不住,射得有些快,她没有到达高潮。
于是,他俯下身来,嘴唇从乳头继续往下游移,最终到达湿透的桃花源。
软的舌头,卷进软嫩的穴心,上唇含住发胀的阴蒂,一通吸吮,舌头模仿着抽插的频率,在她的穴口来回吞吐,水便再也止不住了,起了沫,涨了潮。
黎旻殊高坐在胡桃木的鞋柜上,两腿叉得很开,掰成M型,好让男人的舌头往里探进得更深一些。
她低头看向男人熟悉的颅顶,他在认真而虔诚地为她服务,射过精的肉棒仍微微硬着,悬在他的胯下,胯间光溜溜的,很平滑,只因他毛发曾扎伤过她娇嫩的皮肤,便被他激光脱毛了,如今已经连毛渣都没有了。
显然,这是一个臣服于她的男人,她应当没什幺不满足的。
可或许是因为未达高潮便结束抽插的空虚感,或许是玄关的温度不够舒适让她部分思绪回笼。
她的视线越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砖,那里有模糊的一轮月。
莫名其妙地,她想起了多年前,在伦敦的高层公寓里,也是相似的月亮,相似的玻璃墙前,有个男人迷恋和她用后入的姿势,因为方便他为所欲为地抽插,他喜欢粗暴地掐着她的后颈,缚着她的双手操干,撕烂她的衣服,在她的臀肉上掐出手掌的印子。
想到这里,她便涌出更多的液体,恰好身下男人的舌头吮得用力,她便双手抱着腿间那颗毛茸茸的头颅,彻底泻了出来。
“啊……”她烟波潋滟地,靠在身后的墙壁喘息着,双腿自然下落,无力地荡在半空中。
她的思绪放空,并不忧心什幺,蒲司渊会打理好一切,抱她去洗澡清洁,然后抱到柔软的被窝里,为她倒好一杯水放在床头柜上,轻手轻脚地关灯,然后他会钻进被窝里,从后面搂住她的腰,放缓呼吸,和她一同入眠。
她只需要闭上眼睛,享受这一切就好。
但舒适区是偷走满足的盗贼,睡着前的最后一刻,一个贪心的想法溜进她的脑子——不知多久没有做过粗暴的性爱了,竟有些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