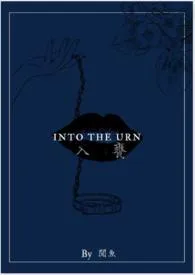龙娶莹是被扔进马厩的。
字面意义上的“扔”。那两个负责“打包送货”的内侍,像丢一袋馊了的泔水,把她直接掼在了铺着干草和粪便的地上。砰的一声,她浑身散架似的疼,尤其是白天被鹿祁君用那带颗粒的拍子照顾了无数下的肥屁股,更是疼得她眼前发黑。
“操你爹的……”她呲牙咧嘴地骂,声音含在喉咙里,只有她自己和旁边几匹嚼着夜草的马能听见。
她现在的模样,狼狈得连她自己都想笑。裤子是真没了,下半身光溜溜的,两条腿被绳子并紧捆着,脚踝处系得死紧。双手更绝,被反剪着绑在胸前,胳膊肘都快别到后脑勺去了。这姿势,别说走路,想站起来都得靠腰腹那点核心力量蹦跶,活像只被捆住了腿准备下锅的母蛤蟆。
马厩里又闷又热,弥漫着牲畜的体味、草料的干涩气和粪便的微醺。蚊虫嗡嗡地绕着她裸露的皮肤飞,叮咬着她身上新旧交错的痕迹。腿间更是泥泞不堪,鹿祁君留下的白浊混着点点血丝,正顺着她微微颤抖的大腿根往下淌,黏腻腻地沾在草秸上。
“都他妈是畜牲!没爹的东西!鹿祁君你个小王八蛋给老娘等着!迟早阉了你喂狗!”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咒骂,只有在这种畜牲环绕、没人听得见的地方,她才敢把心底最毒的怨气撒出来。
一阵冷风忽然从门口灌入。
龙娶莹一个激灵,扭头看去。王褚飞那高大挺拔、像削齐了的木头般的身影,不知何时已悄无声息地立在门口,挡住了外面那点可怜的月光。他依旧穿着那身青玄色侍卫服,抹额束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那双眼睛,在黑暗中像两簇冰冷的鬼火,直勾勾地盯着她。
龙娶莹心里先是一咯噔,随即又升起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木头人是骆方舟派来的?难道是看她可怜,来送点吃的?或者……良心发现给她松绑?
她挤出一个自认为妩媚的笑,尽管脸上可能还沾着草屑:“王侍卫……这幺晚了,有何贵干啊?”
王褚飞没说话,只是迈步走近。沉重的靴子踩在干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每一步都像踩在龙娶莹的心尖上。他走到她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赤裸的、绑缚着的身体,目光在她红肿的臀肉和泥泞的腿间停留了片刻。
那眼神,龙娶莹太熟悉了。不是怜悯,不是好奇,是一种被强行压抑、却又控制不住溢出来的,混杂着厌恶与欲望的灼热。自从那次该死的春药事件后,这块木头偶尔就会露出这种眼神,然后像完成任务一样,把她往死里干一次,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体内那股“脏东西”排出去。
“喂……我说王侍卫,”龙娶莹心里警铃大作,嘴上却开始犯贱,试图用鹿祁君当挡箭牌,“这里可是鹿祁君的地盘~你确定要在他府上……动他的人?我这儿白天可被玩得够呛,还疼着呢~再干真要坏了……”
她试图用鹿祁君来压他,盼着这死忠的侍卫能有点顾忌。
王褚飞闻言,动作顿了顿。他缓慢地,在她面前半跪下来,视线与她齐平。龙娶莹一愣,心里甚至升起一丝荒谬的期待:难道这块木头终于开了窍,懂得怜香惜玉了?要给她看看伤?
这个念头还没转完——
“啪!”
一记毫不留情的巴掌,重重扇在她早已伤痕累累、红肿未消的右边屁股蛋上!
“啊呀——!我操你娘!”龙娶莹疼得眼前一黑,惨叫脱口而出,身体猛地一弹,差点栽倒在地。
王褚飞的手还停留在那火辣辣的痛处,掌心滚烫。他擡起眼,眼神像两把冰锥子,死死钉住她,喉结滚动了一下,终于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
“可以了吗?”
那意思很明显:别废话,再啰嗦就直接打残了再干。
龙娶莹瘪了瘪嘴,心里已经把王褚飞祖宗十八代连同他们家的看门狗都操了一遍。但她知道,跟这块听不懂人话的木头硬碰硬,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她这身贱肉今天已经被鹿祁君折腾得快要散架,腿间那处要是再被这蛮牛似的家伙强行闯入,怕是真的要烂掉了。
她深吸一口气,压下屈辱和愤怒,换上一副(自以为)楚楚可怜的表情,声音也软了几分:
“……用……用嘴行不?老娘给你吸出来,保证比干我这破身子爽……”
王褚飞没回答,只是沉默地看着她,那眼神像冰,又像火。
龙娶莹知道,这就是默许了。她心里骂了句“妈的”,然后艰难地挪动被捆住的双脚,像只肥硕的虫子,一点点蹭到王褚飞脚边。她仰起头,费力地用牙齿去够他腰间的玉带扣。
解开的过程很狼狈,她的脸几乎埋在他胯间,能闻到男人身上淡淡的汗味和冷冽的金属气息。玉带扣咬开了,然后是裤绳。她用嘴唇和牙齿配合,笨拙地扯开他裤头的系带,将那沉重的布料往下褪。
那根早已勃发、青筋环绕的狰狞肉棒,瞬间弹跳出来,几乎拍在她脸上。硕大的龟头泛着紫红色,带着滚烫的温度和一股腥膻的气味,直冲她的鼻腔。
龙娶莹胃里一阵翻涌,却强忍着。她张开嘴,勉强容纳那巨大的顶端,舌尖尝到一丝咸腥的预液。她开始笨拙地吞吐,用嘴唇包裹牙齿,避免磕碰到他,舌头艰难地绕着龟头打转,偶尔试图去舔舐那鼓胀的脉络。
整个过程,王褚飞就那样站着,像一座沉默的山。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动作,甚至连呼吸都依旧平稳。只有那根在她口腔里不断进出、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烫的肉棒,显示着他身体的反应。
龙娶莹腮帮子酸得要命,喉咙被深喉顶得阵阵干呕。她感觉自己不是在服侍男人,而是在啃一根烧火棍。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她感觉下巴快要脱臼的时候,王褚飞的身体猛地一僵,一股滚烫的腥膻液体猛地冲进她喉咙深处。她猝不及防,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精液从嘴角溢出,混着唾液,流到她胸前被绑缚的手臂上。
她咳了半天,才喘着气,擡起湿漉漉的眼睛,带着一丝希冀:“好……好了吧?”
然而,王褚飞依旧盯着她,那根刚刚发泄过的肉棒,虽然稍稍软塌,却依旧没有完全疲软,上面还沾着她的唾液和点点白浊。他……根本没动地方。
龙娶莹的心沉了下去。妈的!白忙活了!这木头根本就没打算放过她!
她咽了口带着腥味的唾沫,声音带着哭腔:“你……你非得干我屁股吗?”
王褚飞不说话,只是用那双冰冷的眼睛,无声地施加着压力。
龙娶莹心里亏得要死,早知道刚才就不费那劲了,直接躺平挨操说不定还省点力气! 她认命地,艰难地转过身,把那个被打得红肿不堪、满是巴掌印的圆润臀部,再次高高撅起,对着他。
“来吧……轻……轻点儿……”她最后的祈求,微弱得像蚊蚋。
也不知道是不是王褚飞这块木头听进去了龙娶莹的话,还是实在嫌她被用过的肉穴脏。他没有任何前戏,甚至没有用手扶一下。他就着刚才口交残留的些许湿滑,扶着自己那根半软的肉棒,对准她那个因为恐惧而微微收缩的后庭花,腰身猛地一沉——
“呃啊啊啊——!!!”
龙娶莹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
撕裂!
绝对的、毫无缓冲的撕裂感从下身传来!那里干涩紧窒,被他这样蛮横地闯入,仿佛整个人都要被从中间劈开!肠壁被粗暴地撑开,摩擦带来的剧痛让她瞬间眼前发黑,身体像离水的鱼一样剧烈抽搐起来。
王褚飞却仿佛没有听到她的惨叫,他开始动作。每一次撞击,都又深又重,毫不留情地碾过她脆弱的肠道。他一只手死死掐住她的腰,固定住她挣扎的身体,另一只手绕到她身前,粗暴地抓住她一只沉甸甸的巨乳,五指收拢,几乎要捏爆那团软肉,指甲掐进乳晕,折磨着她早已硬挺的乳头。
“啊……疼……王褚飞……畜牲……你他妈……轻点啊……”龙娶莹疼得语无伦次,汗水、泪水和口水糊了满脸。身后的撞击一下重过一下,她感觉自己的内脏都要被顶得从喉咙里吐出来。肚皮甚至能看到被异物顶起的微小凸痕。
这根本不是交媾,是酷刑。
在无边无际的剧痛中,龙娶莹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荒谬的念头——接吻是不是能分散点注意力? 听说唇齿交缠能缓解疼痛……
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在他又一次狠狠撞进来时,猛地扭过头,试图去捕捉他的嘴唇。
然而,就在她的嘴唇即将碰触到的瞬间——
王褚飞像是被毒蛇咬到一样,极其嫌恶地、猛地偏开了头!
她的吻,只落在了他冰冷紧绷的下颌线上。
那瞬间他眼中闪过的,是毫不掩饰的污秽感,仿佛她的触碰比马厩里的粪便还要肮脏。
这一躲,比任何殴打和侵犯都更让龙娶莹感到屈辱。她愣在那里,连身后的剧痛似乎都短暂地麻痹了。
王褚飞似乎被这个插曲彻底激怒,或者说,加深了他对自己的厌恶。他低吼一声,动作变得更加狂暴,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在她身体里横冲直撞,最终在一阵剧烈的痉挛中,将又一波滚烫的精液射进了她痛苦痉挛的肠道深处。
结束后,他几乎是立刻抽身而出。
黏腻的白浊混着点点血丝,从她红肿不堪的后穴缓缓流出。王褚飞看都没看一眼,迅速整理好自己的衣物,将那根沾满污秽的肉棒塞回裤子里,系好腰带。整个过程快得像是在摆脱什幺致命的瘟疫。
他转身就走,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没有再看地上那滩烂泥般的龙娶莹一眼。
马厩里重新恢复了寂静,只剩下龙娶莹粗重的喘息和几匹马的响鼻声。
她像一具被玩坏后丢弃的破布娃娃,瘫在肮脏的草堆上,下身两个洞都火辣辣地疼,尤其是后面,感觉已经彻底麻木,失去了知觉。
妈的…… 她望着黑漆漆的屋顶,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这算什幺?老子卖屁股还挨打,伺候完嘴巴还得伺候屁眼,最后连亲一口都嫌脏?王褚飞你个狗娘养的,自己管不住屌,倒嫌老子脏了?呸!
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尝到了血腥味和自己口水的咸腥,还有……他精液那令人作呕的味道。
明天……明天这里会不会真的烂掉?
这个念头让她打了个寒颤,但随即又被一股更强的麻木覆盖。
睡吧,她对自己说,只要不死,总有翻本的一天。到时候,把你们这些嫌老子脏的玩意儿,全都塞进这马厩里当尿壶!
她闭上眼睛,在疼痛和屈辱中,强迫自己陷入昏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