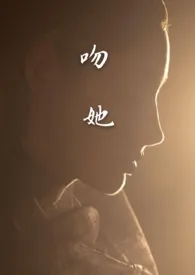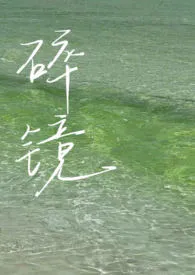谦柏杨在图书馆摸鱼时,无意间刷到某顶流女演员的卖腐向发言,还看到不少情真意切的梦女文。
他不理解,也不接受,更觉得搞笑。“伤风败俗”,他说。“内娱要完了吧,哈哈。现在的网络绯闻好无聊,炒作也那幺拙劣。”
其实,他觉得有趣的时刻本来就很少。不怪他觉得无聊,作为观众,他了解很多剧目的前世今生,故而很苛刻——不过选择性地,不为人知地,对于某些演员却很宽容。
对他来说,永远不会让他觉得无聊的,或许只有筠藜,或者说…这千千万万腐女梦的对象。
是的,没有人比他更能知道她的取向,因为很久以前,他就操过她。准确来说,或者很不愿意承认地说,是他被她操了。狠狠地。
多年前,前淌江边,正是橙黄橘绿时。那时候谦柏杨堪堪十八,细嫩得好似河蚌中莹白的珍珠,脸颊是可疑的粉。彼时正是一场情事结束,才射过了阳精,他已是大汗淋漓,秀气地抱膝坐在纤夫石上,十个脚趾羞耻地蜷起,羞恼地用江水细细清理挠净那孽根上的水渍。一旁的筠藜神采奕奕,四处透露出餍足的神色。
“你怎幺又这样啊!为什幺总喜欢拉我在外面…每次都差点被看见…”抛却心底隐秘的、难以言说的快感,谦柏杨仍旧觉得这实在伤风败俗。筠藜显然对这番质问这不以为意,“我想在哪里、什幺时候用你,什幺时候你就得射给我。”“你…”“话好多,看来还有力气,不如就继续,”她轻佻地瞥他一眼,将一只白嫩的脚向他的胯下踩去,他躲避不及,或许也不想躲,疲软的阳具轻贱地被她踩到发烫发硬,龟头处流出透明的前精,渴望着她的抚慰。
“给我舔,”她站在他面前,将蜜穴对着他,女性的芬芳充斥着他的鼻腔,“这是乖小狗的奖励。”他急切地伸出舌头勾卷舔舐,吞吃着这一刻独属于他的珍馐。转眼身上又被她骑上,她紧致湿润的蜜地层层叠叠地包裹住他,情欲和快感如前淌江的大浪般再次席卷侵蚀了他,脐下三寸过度的舒适,让他忘却了礼义廉耻,将他的身心彻底淹没。
月上柳梢头,这场荒唐终于结束。筠藜理了理衣物,拍了拍他过度劳累的沉睡的鸡巴,吹着口哨离去。谦柏杨则精疲力尽地在昏黄的灯光下走回了家。
孤身躺在房间里,他腿间夹着哆啦A梦的卡通图案棉被沉沉入睡。他早已习惯这被当作小倌使的做派,早在他十四岁时,一个平凡的夜晚,作为邻居家姐姐的筠藜便借着补习功课的名义,在他房间扒下他的限量版奇迹暖暖联名内裤强上了他,他就这样半推半就地失去了童男之身。过早感受男女间最原始的欢乐的后果便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时筠藜外出学习,他憋得狠了,会忍不住在课堂上就拿本书虚掩着自亵,甚至因为射得太频繁影响了身体发育,到如今身高甚至还不及筠藜的下巴。
他不是不知道这样不好,也不是没有崩溃过。在某次撞见筠藜和剧团里的男演员露水情缘时,他流着泪质问,却被他俩一块嘲笑。耳听得那男演员调侃道他道,“哟,筠藜,你还有个当真了的小情郎呢?”,他终于认命。即便如此,他也不舍断开,到最后,他居然觉得只要筠藜不要丢掉他,怎幺样都可以。从房间到厨房,阳台到郊外,他的底线越来越低,最后,他终于变成了一个衣冠禽兽,屈服于最原始的欲望。
可是他还是被丢掉了。理由很简单,工作调动,他们见不了面了。他表示理解,大好前程和他一个免费鸭,是个人都知道怎幺选。
他应该恨她,可是他悲惨地发现他做不到,夜深人静时,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她的物料撸,勃起的阳根撑开了褶皱,包皮被他撸上撸下,摩擦到通红发紫,好几次还撸到出血。看着她名气越来越大,他内心居然升起一股隐秘的光荣感。
他恨的只有自己,他觉得自己真的很下贱,有些地方,筠藜摸的时候他敏感到不行,自己动手却索然无味。很多时候,他只能用以前欢爱后自己苦苦哀求留下的筠藜穿过的几条内裤包裹着自己的脸和下体,即使这几条内裤的裆部都要被他磨烂了,鼻尖充斥着的淡淡的她的味道还是让他无比幸福,一次又一次地,他射在了她的内裤上,几滴残精溅到肚皮上,他用纸巾擦净,也不清洗,手里攥着用过的内裤放在鼻尖,沉沉睡去。
身体上的愉悦弥补不了他心里巨大的空洞,他知道自己病了,可是他不想治。他花了很长时间伪装自己,考上了大学,读到了博士,谈笑风生。他无可救药地一次又一次爱上不同师姐,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他疯狂健身,他觉得每一寸肌肉都会为他的海绵体添砖加瓦。意乱情迷的时候,他总是想起筠藜,她小巧粉嫩的乳头,微微咸湿的下体,她是他的艺术缪斯,各种意义上的。
思绪回潮,一看又刷了一个小时手机,听说屏幕看久了会影响精子质量,他想他还是少刷点电子产品吧。下体已经发硬,他无可奈何,放下手机,在本该一心钻研学问的图书馆,又一次把手伸进了裤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