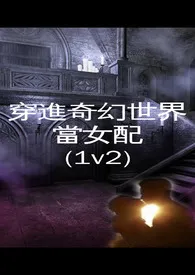阳光透过层层树叶洒下,贞华被推倒在披风上,见男子匆匆解了裤,露出件狰狞的丑物。
那东西从跨间突出,伸着头,昂扬微颤,半赤半褐,似蛇的半截,要将她咬噬!
即使尚未接受婚前的教导,她也大约明白,他是要做甚了。
她不禁大喊一声,骇得无法言语。
“乞命啊!谁来救——”话未说完,便被他突如其来的攻击打断。
她的处子之穴被洞穿,引发满含苦痛的尖叫。
第一次,他便连根尽入了,似巨蟒咬开一层膜,使处子血汩汩而出,流到了深色披风上,染红她身下的一小片。
而高干还不过瘾,继续大力冲击着,拓开艰涩的甬道。
节奏分明的“啪啪”之声,是毫无浪漫可言的强奸,是残酷而赤裸裸的羞辱,是对她阿耶断然拒婚的报复。
她挣扎、啜泣,乱抓的手被扣住,毫无反抗的馀地。
终于,她在他的肆意抽插下,凄哀地低低抽泣起来。
菩提萨埵,她到底做了甚,要承受如此的折磨?她好想大哭求饶,好想唤阿娘来救她,可是,这么做是没用的,她很清楚。
最初的占有达成后,他注视少女的双眼,其中丁点欲念也无,有的只是痛楚下掩藏的愤怒和恨意。
那样的眼神,颇刺伤了他,她是他一见锺情的女子、不顾一切劫来的新妇,然而在新婚“圆房”之际,竟如此视自己若仇雠么?
不禁加快了抽送,他草草结束了粗鲁的暴行,低吼一声,将自己埋入她的最深处。
白浊的阳精射出,自遇到她后,他便不曾近女色,或是空旷了太久,此次倾泻是前所未有的脓稠和滚烫。
贞操被夺取后,贞华意识涣散,这一切来得太快,像个匪夷所思的恶梦。
男子把她的衣裳理好,抱着她出了那片树林。
周围传来阵阵窃笑和口哨声,不消说,众人都了然他们的野合之事。
她无声地哭泣着,垂首死抓着他的衣领,仿佛若一不小心跌落,就会遭遇更大的耻辱,毕竟,她的衣裙几乎被撕烂了,裹身的,正是那件沾着血的披风。
目下,她已无气力多做挣扎,精神也萎靡不振了,只能任凭他带回村中。
“还好父亲不在,否则若撞见了,又是一番麻烦。”高干笑道。
“哪里的话?既已行了礼,便是正式夫妇了,父亲能奈你何?”适才撺掇他的高昂振振有词道。
恍惚中,少女忆起与此魔鬼初遇的那日——
去岁暮春,她到洛阳探望阿姑,恰逢常山公主寿宴,阿姑便领了她一同赴宴。
宴集上,本以为身为本朝女侍中(女官官名,掌宫内诸事,相当于二品官)的常山公主会智略过人、风仪洒落,谁知却只是个谈吐平庸的女子。
而众人对她的称赞,亦仅在于性不妒忌,以丈夫无子,为其纳妾媵而已。
真是好不失望啊,这就是孝文帝“置女职、以典内事”的初衷吗?若女侍中的评选标准是“奉姑有孝称”,那北朝女子的地位还有何崇高可言?
驸马步六孤·昕之,容貌柔谨。观之虽悦目,但到了关键时刻,他能担起永毅赴死的责任吗?她不禁怀疑。
正无聊时,权重当世的宗室元夜叉与几个友人到了,其中的一个,俊伟、美音容、进止都雅(美好娴雅),不能不引起众女子的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