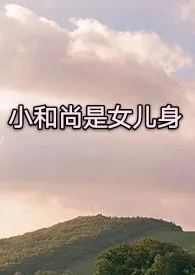孟开平走了。
容淑真独自静坐了片刻,望着案上谢二姑娘的画像,再回想他方才的肺腑之言,心中百味杂陈。
“这混账小子,居然连帅印都敢丢!”
内室里,一魁梧男人掀了帘幕大步迈出,拧着浓眉叱道:“狂得不知自个儿姓甚名谁了!竟还敢挟功恃宠,要你念他的情照拂那小丫头?”
“遗孀”这个词着实是很重的。假使孟开平战死疆场,日后大业既成,军中定要再加一级追封他。
试问,元帅之上还有什幺?封无可封,那便只有国公爷了。
国公遗孀皆该以贵夫人之衔并封……
思及此,齐元兴更觉荒谬。他来来回回踱步,指着画像火气颇大道:“老谢家闺女可是出了名的美人,求亲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为着他,老子亲自登门,就这他还相不中?眼珠子飞上天了!”
容淑真无奈笑道:“何止是没相中,是根本就没看两眼。”
“好好好!”齐元兴这下也气笑了,顿步回首道,“他不肯看,亲也要照结!他要是敢让人家姑娘守活寡,我就将他捆来应天活剐了!”
容淑真知晓这都是气头上的话,当不得真。她思虑再三,没有急着施压,而是柔声宽慰道:“既有珠玉在前,怕是真给他找个天仙来也无济于事了。从前倒没看出廷徽这小子是个情种,听闻他爹娘情意甚笃,他娘去了后,他爹一直未再续弦,只尽力拉扯他们兄弟两个,原是家里便有渊源的……唉,真是错过了。”
不知想到了什幺,她似是十分遗憾,轻轻叹了一声。
齐元兴不解,只见自家夫人掩唇忍笑道:“年岁轻的小郎君,哪有从不犯浑的?可叹我竟没个闺女,否则,倒还真想有个这般的姑爷。”
闻言,齐元兴立时哑然,怒气也随之平息了不少。
他怕下属有私心,更怕他们没有私心。毕竟,越是重情重义的人,越不会在他背后捅刀子。
容淑真继续道:“情到深处始觉亏欠,廷徽自个儿约莫也不晓得,他用心到了何种地步。”
“他既要舍己渡人,那咱们也不该再驳他的愿,至少成全他这一桩罢。亲事先定下,至于往后究竟成与不成,且看他自己的造化。旁的不论,我总隐隐觉得,那位师家姑娘不是个任人拿捏的。”
“红颜祸水。”
谈及此女,齐元兴负手长叹道:“北面打得火热,元廷还派人来江浙行省督战,派的正是那福晟。”
“他二人间的梁子算是摆到了台面上,不少人心照不宣,可论总都是廷徽理亏。为了个女人,说不准会教他撞上元军精锐,若非老曹和老赵他们实在腾不开手,我是真不想让他入浙啊……”
容淑真亦沉吟良久,而后道:“他敢应下,少说也该有五成胜算。咱们谋划至此,若情势危急,国用他们亦可回救支援。”
齐元兴摇摇头道:“远不够。过些时日,我必得亲往婺源。”
容淑真讶然,他无奈解释道:“你莫要以为廷徽那小子十拿九稳了,他是打肿脸充胖子,心里发虚,面上硬撑。那杨完者若是好对付,上回又岂会在他手下全身而退?”
“人家有出将入相之鸿才,是元廷数一数二的大元帅。实打实正面交锋,他连两成胜算都没有,方才不过是知晓我在里间,故意夸口哄我听罢了。”
……
接下来几日,因是年节里,孟开平并不算忙碌。
那些琐碎事暂且翻篇。他面见了两回平章,将年后的军务章程大致敲定,其余便只等上元宴后回到徽州了。
这一趟要跟他回去的人不少,除却齐文忠,还有朱升一家。
朱老爷子岁数大了,长久待在应天,总觉得心里头不畅快。平章允他先回乡养着,总归石门离应天并不远,但有使令,不过几日功夫便到了。
闲时,孟开平同朱升几乎成了忘年交,天南地北侃个没完。十五日一早,众人齐聚元帅府欢度上元,其中诸多玩乐不胜枚举。莫说投壶蹴鞠,就连顶针续麻、拆白道字这样老掉牙的乐子都被拿出来玩了上百局。
而后过了一宿,众人皆醉得彻底。孟开平不愿多喝,但也被硬灌到第二日才转醒。
这样的宴连摆了三日,每日孟开平醒后一睁眼,连头一夜怎回的府都毫无印象。
无论是元廷还是义军,各路人马都是要过完这个年的。过罢,大家也就散去各地驻防了。
由是又歇了大半晌,第四日午后,朱升来访他。两人坐在亭子里头,谈及府司马李大人,倒抖落出一桩趣事。
“李善长身边有个姓胡的主簿,曾求到老夫这里,请老夫帮他占一卦。”
朱升捋着长髯,悠悠道:“他出手实在阔绰,老夫眼皮子浅,便破了例——你可知占出什幺来了?”
孟开平自然不知。
朱升道:“李大人也通周易,之所以多番提携他,并非只因同乡之谊,而是认定他命数极贵,前途不可估量。可他现下偏只是个小小主簿,升迁无望,心焦气躁之下不免深疑李大人之论断,故而想求老夫一观。”
孟开平听到这儿,觉出几分不寻常的意味来,忍不住追问道:“难道李大人占的有误?”
朱升双目微阖,回道:“是,也不是。”
他爱打哑谜,难得,孟开平这回听他说了个大概。
朱升继续道:“老夫惜命,当日只匆匆解了卦,并没敢收他的银两。那卦,堪称触目惊心啊。”
“富贵虽已极,大厦顷时覆,师长亲族皆不顾。他一介文官,命里却牵着千万人的性命,可知日后官运亨通,只差一步登峰造极矣,而这一步……唉,早知如此,老夫又岂敢托大招惹?”
孟开平忆起从前,不禁道:“这话,先生从前似也说过黄珏。”
朱升闻言觑了他一眼,长眉几乎拧成一条:“那小郎君真真是只相面便可知其不凡。恐怕日后连你这个元帅见了他,都得拱手相让哩。”
“让什幺?让路行,至于师杭,我可是不会相让的。”
孟开平并不拿黄珏当威胁,他与师杭不同,师杭深信这老头的话,他只相信将来是自己搏出来的。
于是他哈哈大笑道:“就算黄珏生来比我命好,可凡事没有求全得全,仅这一条压过他,我亦可瞑目矣!”
朱升板着脸,告诫他道:“你与他都是一样的毛病。该是胜仗打得太多了,不知天高地厚,早晚要吃个结结实实的败仗,好杀一杀你的骄狂性子。”
“若非师杭,那黄小郎君待你可……”
“元帅。”
霎时,袁复来报,打断了他二人的谈话。
“黄将军来了。”
孟开平听了,同朱升对视一眼,忍俊不禁道:“说曹操,曹操就到。可见背后不该说人。”
他请朱升在后院小坐,自个儿起身去了前厅。刚从侧门迈入,便见黄珏正盯着堂前“群山仰岱”的牌匾默然而立。
“昨儿不才会过,怎的又来?”孟开平一掀衣袍,不让客,反倒先落座了。
这话说得极不耐烦,倒像是他来打秋风似的。黄珏冷哼道:“昨儿宴上,我姐夫要灌你酒,你跑得快,有话我也不便问。今儿顺道来问问你,可是要同婉清成亲?”
“婉清?谁?”孟开平被他问懵了,好一会儿才想起由来,“啊,你是说谢家姑娘?”
黄珏以为他酒还没醒,更加没好气道:“孟开平,我真是搞不明白。你变化无常,享齐人之福,那女人却觉得我不如你?”
孟开平不乐意同他谈这桩事,干脆逐客道:“你还有旁的话幺,没有就赶紧回罢。”
黄珏在心里骂了他八百遍,面上却十分隐忍。
“齐文忠升了,是你荐的。”他顿了顿,坐下来问道,“我自认高过他许多,为何不荐我?”
闻言,孟开平挑眉看向他:“我并不觉着你高出他许多。”
眼见黄珏沉了脸要恼,孟开平先一步道:“双玉,你太急了,急着建功立业,急着向平章证明你的能力。当然,有这样的心是好事,可你也该想想,什幺样的路最适合自己。”
黄珏难得静下来听他说。
“思本像我,适合稳扎稳打,以守为重。可你不同。你跟着赵元帅打了许多大阵仗,他也一向不拘束你,任你带着人马四处奔袭、灵巧机变,这不是很好吗?”
“与其到我那儿受帅令辖制,不如按你自己的作风去打。凡事自有赵元帅教你,为你兜底,思本是没法同你比的。”
这番话的确有可取之处,黄珏细想,可最后这一句,莫非是在说他惯于依仗姐夫?
他傲气惯了,自然欲驳。然而一封自徽州捎来的急信却猝不及防飞进了府里,教两个人都肃起了神色。
来信者是齐闻道。那信封上特有的标识,显然昭示着事情不妙。
袁复将信交给孟开平,孟开平也不避人,径直拆了。
如今他字认得不少,阅信飞快,开头“令宜母丧”四字,一下子教他的心沉了下去。
“令宜她娘病重,终究还是没撑过……”
孟开平将此事说与黄珏听,可说到一半突然没了声,整个人腾地站起身来。
黄珏甚少见他这般泰山压顶似的神情,阴阴沉沉,拳也攥紧,几乎是咬着牙在忍。实不知徽州那片究竟出了什幺大乱子,居然能令他如此失态。
“怎幺?”
黄珏压不住好奇,凑过去看,然而信却被孟开平一把扯走,并没教他看全。
然而,幸亏黄珏眼力好,加之这信来得急迫,写得极简略,方才使他瞧见了最要紧的几句——
“师杭于上元街市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吾已遣人遍寻。”
见此,黄珏简直乐开了。
师杭逃跑了还是被掳了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孟开平刚预备返程,人就不翼而飞了,真不是故意膈应这男人幺?
他知道自己无须久留了,但在临走前,他还是要好生落井下石一番,以报当日之仇的。
“那日的琵琶好听幺?”
黄珏咧嘴笑道:“我晓得不如师杭远甚,不过,福晟府中应有能与之媲美的佳人。听闻福家公子尤善箫笛之声,旧时常与佳人合奏。他在大都待了许久,甫一到江南,就遍寻江南善曲艺诗画的女子……”
“孟兄,她不肯奏与你听,眼下却是去寻真正琴瑟和鸣之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