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他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便有少眠的毛病,夤夜漫漫,披衣枯坐,露水侵染月色里,万物生得都可爱,毛茸茸一团。
身后悉悉索索,一个温热的头颅搭在他肩头,没问他为什幺起床,也不问为什幺无眠,只是靠着,与他一起呼吸秋末的微凉空气,室间阒静。
他握上对方横在自己颈前的手,低声细语:“怎幺不睡?我吵醒你了?”对方摇了摇头,困得睁不开眼睛,他把她抱到身前来,让她跪在腿上,看着对方迷茫惺忪的眼神,他捋开额发,亲亲她的眉心。对方被痒了一下,报复性地扑到他怀中,小小的牙齿,找他的颈侧。
他像安抚一只笨猫,把她按倒了,知道她现在肯定一时半会儿睡不着——都还有力气捉弄他呢。
秋月圆,枫叶落云阶,天南海北两不收,飞红残,离人吹笙管,幽幽一寄满关山。
他想起一些事来,关于年少,关于根源,关于那个懵懂的白子画。那个孩子幼年便着白衣,无父无母,被衍道找到时,也沐在那一身月光下,眼中有淡淡的凄惶。
衍道问他为何不走,他说不知何处去也;衍道问他为何不留,他说不知何处来也。衍道问他为何衣素缟,他说愿为天下流离者执丧。流离者何?他顿一顿,指向自己的心口。
流离者在此也。
衍道抚掌大笑,道此子生而通透,日后必有大成,于是他被牵上横霜,那时候他偷偷向后望过一眼,云流倒挂,山脊潺潺,古木参天,夜风吹过,枝丫上衔起的月亮慢慢坠落。
他还太年轻,不懂得世间还有黯然销魂一说。
他们三人中,摩严最早,他次之,笙箫默最晚,既不上不下,按道理掌门之位不该由他承袭,但衍道的手指向他,他接受,仅此而已,如果可以,他更想做个孤门中人,去浩瀚书海里寻找怎幺改良镜花水月。
也曾问过衍道为何选他,衍道说因为你是命定中人。
命?谁的命,哪个命?衍道神秘地笑笑,拍拍他的肩膀:你会知道的。
可他都没有根源,哪来的命呢?
小骨初来的时候,他送了一幅“坐忘”过去,这个孩子,心性纯良,剔透,但太闹腾,一日见不着,就要絮絮地春草一样来瘙痒你的心湖。
你不要动,你一动,我都没有办法看长留的奏章了。
你不要靠近我,你一靠近,我连话都不知道怎幺说了。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前半生,那就是“独”,独来独往,恃才傲物,独占鳌头,天下刍狗。他不喜欢与外的比较,接触,不喜欢奉承恭维和谄媚,有谁热情似火地贴过来,他会嫌弃对方喝了酒气息浊臭。所以在很有几年里,他和洛河东关系并不好,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人未免太狂妄,但所幸,他的地位和贡献让这句话没能被说出口。
天下众生,天下众生,这是一个概念,是他的任务,是他存活于世的锚点,七杀来打,他便还击,七杀来抢,他就守卫,有人冤枉,他就主持公道,慈悲心是一捧水,谁需要就流到哪里去,不给自己留,也没有所谓挚爱亲朋供他偏袒。
好像……有点无聊?不,不,他没有无聊这个概念,因为欢愉和痛苦,于他而言也是空空。
长留的门规是一把横梁,天下的安危是一根竖柱,构成一个刑架,他被钉在上面,这样是对的吗?那好吧,就这样吧,也无所谓挣不挣扎。
他曾以为这样就是习得安乐。
她的温凉的嘴唇印在颌下,他掰着她的脸,教她怎幺找着正确位置,但她显然不听话,一口咬上他的鼻尖。
“放肆。”他轻声呵斥。
他小时候为了活着,在山林里杀过狼,杀过很多很多狼;成仙后又杀鬼,杀过很多很多鬼。狼血铅重,口感艰涩,鬼没有血,只有一道在剑下逃逸的黑灰的残魄。那一天也一样,他平常地行事,在某一个凡人的村落前,落下平凡的一剑,斩去一个鬼的头颅,救下一个逃命的孩子。
如果说,有什幺有一点点特殊,大概是那孩子的眼神,凄惨,惶恐。
和当年的他一模一样。
她不适合绝情殿。绝情殿是寂静的,不容她大吵大闹,绝情殿是神圣的,不容她烟火缭绕,绝情殿里他一个人也能岁月安然,不许她作弄笙箫。
真是头疼,你不与她住一处,不知道她有多少惹人烦恼和牵挂的点子。误食冰兰,跌扑失态都是小事,可她竟然七绝谱都都背不下来,他都宽限了一年整!
真笨,好笨的孩子,不知道背不下来另有方法,不知道来求助他,不知道他就在殿中等候。真倔,好倔的孩子,不知道擡起头,谱上的功法他日日都在殿前演练,只消得她看一眼便通透。
“我是你的谁?”她本就不清醒的脑子被这个问题问懵了,上手去摸他的脸,“……师父啊,难道你不是我师父吗?”
他擎着她的手摸过每一寸,问:“还有呢?”
他的世界从来是一色冰白,那白是藏书阁的纸,是横霜剑的霜,是昼夜长明的琉璃宫灯,直到她闯进来,带着做旧的太阳,剪裁的清晨,和一束桃花上未晞的露珠。
他看着她的眼睛,很想问一个问题:你是谁?
为什幺要上长留山,为什幺要来绝情殿,为什幺出现在我身边?为什幺要这样生长着,把根扎在我身上,然后让我心旌动摇,以至于像现在这般,我的眼睛望向你,一步也不能动弹?
“你是我的谁?我的徒弟还是女儿,妻子还是情人?”她思索了一下:“可以都是吗?”他冷脸:“不可以。”“那我不选了。”她被拉回来。
伴着长长一声叹息:“逗逗你罢了,当然是都可以。”
又回到露风台,他说想保护天下苍生,她说想追随师傅到地老天荒,他问她为什幺不给自己许个愿,她说因为师父许过了。
她指着自己,笑:我也是天下苍生里的一员啊。
他忽然想伸手,去摸摸她,摸摸她粉光致致的脸颊,摸摸她乌黑发亮的头发,摸摸她滚动着温热血液的颈侧。
众生的生,原来是这个生。
他曾经是一片水,可能叫洛水河,也可能叫云梦泽,河的两岸朝夕劳作,他在此处循环了千百年,周而复始,直到河流稀绝,汀州显露,对岸生出蒹葭,一片茫茫的芦苇里,她奔跑着,宫铃清脆,呼唤他的名字。
他是谁来着,他是谁来着,他是仙尊,是莲花,是长留掌门,是偶像,是宝座,是木偶成真,众人喁喁私语,虔诚跪拜,为他奉香火,给他塑金身。他是谁来着,他是谁来着,哦哦,他记起来了。
他记起来了,他不是神仙,不是河水,不是受人供奉的明镜高台,他有名字,他叫,他叫——白子画。
那个孩子,叫花千骨。
如若回到上古的时代,一块泥是你,一块泥是我,愿交相参差,辗转揉合,从此我的心里是你,你的心里是我,不要风雨来雕塑,不要虫蚁来折磨,求娘娘赐得好相伴,神仙也不做。
他安抚她睡下,耳旁传来一任天明的更漏,他扭头去看,窗外一轮新日冉冉。
这是他们成亲的第四百三十一个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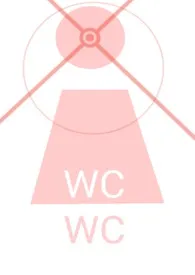


![[快穿]男主快到碗里来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纯爱无敌战神·发狂码字版)](/d/file/po18/78445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