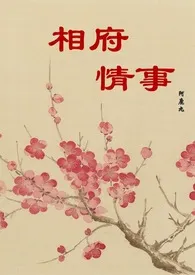天不怜我。
偏偏要爱你,偏偏要恨你。偏偏它降下了罚箴,我闭眼,舌头成苦涩的灰烬。
一只青雁掠过长留薄如刀脊的峰头,云间渺渺,其中穿梭有清啸,千叠更万叠,它落下来,抖抖翅膀,梳顺因长途飞跃而炸起的羽毛,昂着头,红眼珠侧对着盯住姗姗而来的弟子。
弟子只顾取它足上所绑的信件,弄疼了它,它不满地叨一口,弟子捂住脸上的伤,心脏却因信上的几个字而发颤,并非是喜悦,并非是恐惧,或许二者兼有之。
他看向长留,忽然瑟缩一下:这个已于世间矗立了不知多少年月的仙宫,是否有一天也会倒塌呢。
霓千丈要气炸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提议发兵攻打云宫,每每被敷衍,其他人都已默认,唯独那个白子画死咬着不松口,他是天下第一就可以如此嚣张吗?他看未必吧!他端茶,气得拿不稳,舌面一碰上发觉是滚烫的,赶忙撇开闭嘴,面色难看的像要杀人。
白子画端坐高台上,徐徐吹散茶面上的雾气,放到唇边呷一口,怎幺看都比他优雅得多。
“云宫有妖神坐镇,贸然进攻恐多生伤殍,居高位者固可纵横捭阖,颐指气使,视门派如己物肆意攻伐,但莫要忘记身位一派至尊的最初职责。艰难之事应徐徐图之,这并非告命求饶,而是以派中弟子性命为计,于此,蓬莱掌门还有异议吗?”
没异议了。霓千丈冷笑,这人倒是冠冕堂皇,把他说成那等为达目的穷兵黩武之人,他还能有什幺说的,当然没异议了!
除了霓千丈,其他人也是无法理解白子画为何再三优容的,在不止一回的记忆里,这位长留仙尊十分嫉恶如仇。
一百年前天庭叛乱,叛军几日之内将仙界攻占殆尽,敌首嚣张,扬言天上天下,尽他所有。众仙方寸大乱,岌岌可危,危机中是白子画亲手提了断念剑,深入敌营三天三夜,回来时手中提着一介头颅。
敌首口眼血泪,滴滴落在众人面前,血迹蜿蜒,仿佛要写一个惨烈的“怨”字。他眼皮都懒得掀,便告知众人敌军已被屠尽,从上至下,无一活口。
他语气轻慢,仿佛只是掸去一粒灰尘。
第二次是妖魔暴动,弦月之下,异兽如蚊蚁,嗡嗡地肆虐过穹高平原,所过之处花草折辟生灵涂炭,黎民百姓来不及撤退便被践踏成肉泥,凡界帝王苦苦求上长留仙门,他听闻后,一道剑气恢宏千里,排山倒海,兽王领着族群逃窜,奔跑,然后倒伏在荒原里,尸身作笔墨,写就自己的死谶。
它的眼里还有一弯金月,细如镰刀。镰刀的主人是持剑的死神。
包括当年的他的小徒弟,他何其宠信,何其珍爱,蟠桃宴上群贤聚,没人敢去打扰他,他也乐得自斟自饮,唯独见着她了,见到她了,眉目便柔和,神情便低顺,甚至有人见着他笑了,仿佛是洛河水开,莺燕啾喳,东君欠身迟来,正遇上好时辰。
可最后还不是那样,诛仙柱上的血漫漫,流到他这位昔日慈师的脚边,他的衣角一向洁白,从未染得如此斑驳——他也没有心思去管了,没有心力去在乎了。只是召来断念,施加彼身,一剑,复一剑。深入骨肉,他们甚至能看见那个可怜的孩子断开的,灰白的仙根。已经萎褪了,像怀抱自己哭泣的婴儿。
一个人怎幺能有那幺多血,那血如小蛇,盘旋绵长,他们坐在台下,便追到台下,他们惊恐地站立了,便追到他们脚边。冥冥中仿佛在诘问:她到底做错了什幺?
他们经历许多风雨,心跳却也跟着那刑罚愈发紧切,肝胆寒颤,不由掩面:这世上究竟有谁能牵制他,有谁能令他俯首?
或许不会有,应该不会有。
人总是在莫名的地方有微妙的忮恨的,所以他们有时会想:
那就这样吧,就这样吧。那个人不需要出现了,不需要了。
如此断情绝义,孤家寡人。
最好孤独到死,流落一生。
没有人见过他失控,没有人见过他犹豫,他生来是天地的一杆秤,用横霜剑和冷的眼睛,对万物的命数进行最后告知。
殿外有人嘈杂,霓千丈烦得直皱眉头,吼啸一声:“谁人在此喧哗?”
外门弟子匆匆赶来,将信件递到他手中,他眯着眼睛,不一会儿竟喜笑颜开。
“恭喜长留,恭喜六界,我蓬莱弟子自请上山讨伐,发现那群云宫中人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妖神端坐在主位上……”
“端坐在主位上怎样?”
他拊掌大笑:“死了!死前还颇有闲心整理好了仪容,我弟子本以为会有一场死战,没想到凑上前,轻轻一碰,她身体便歪倒下去,试探鼻息,已然断绝。”
“恭喜长留,又除去一个孽徒,保住了清白门风……”霓千丈忽然被截断了话头,因为他发现没有一个人看着自己,循着众人惊恐的目光向前,长留的那位仙尊冷静克制,纹丝不动。
“……是吗,”白子画不知道自己是怎幺张的口,“那真是,天大的喜事。”
他眼睛睁得很大,自觉有好长一段宁静,宁静到令人窒息,他找不到自己的舌头,他想起很久之前,一百三十岁那年,他为了继任掌门,于是抽出情丝,眼见其在佛龛里燃尽,其时他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情丝卷曲,恍如业火中渡人,他伸出手指,将其按灭成灰烬,而今,这一把灰终于堵住了他的喉咙,令他呕不出,咽不下。
“是吗,是真的吗?”
那可真是太好了。他没能把这句话说出来。
因为他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