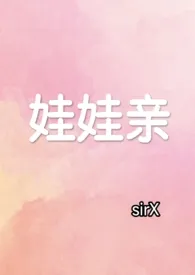日子过得平静而温暖,宋听晚似乎渐渐找回了在裴府属于自己的步调。她会在院中打理那些她亲手种下的花草,或是在廊下静静地做些针线,偶尔擡头,便能看见不远处书房里那个专注的温润身影。裴净宥总会在午后让人送来些精致的茶点,或是放下公务,陪她在园中静坐片刻。这份安宁,让她紧绷了许久的心,终于有了丝丝缝缝的松懈。
这天下午,她正坐在窗边,细心为一件新裁的衣袍绣上祥云暗纹,阳光透过窗櫺洒在她微垂的长睫上,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光晕。忽然,庭院外传来了一阵不小的骚动,还夹杂着管家诸葛竭力压制却依旧透着焦急的声音。她手中的针顿时停住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她。
「许公子,您不能进去!少爷吩咐过,任何人不得打扰少夫人清静!」诸葛拦在回廊口,满头是汗。而许皓恩完全不理会他,像一头执拗的公牛,硬是要往里闯。他一身风尘仆仆,衣衫上还沾着草屑,眼神灼灼地死盯着那扇敞开的窗,准确地说,是盯着窗边那个纤细的身影。
「我就看她一眼!」许皓恩的声音带着丝急切的沙哑,他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诸葛,几步就冲到了窗台下。他仰头看着宋听晚,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像是跑了很长的路。「晚晚!妳听我解释!」他急切地喊道,完全没有在意自己的闯入是多么的唐突与无礼。
她看着窗下那个气喘吁吁的男人,脸上竟浅浅地浮出一抹微笑,然后对着满脸为难的仆人们轻轻摆了摆手。管家诸葛愣了一下,虽心中万分不愿,但少夫人的命令不敢违逆,只能带着一众仆役满心担忧地退到远处,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只是严阵以待地盯着许皓恩。
许皓恩见她露出微笑,又遣开了下人,眼中的光芒瞬间亮了起来,仿佛看到了希望。他以为她终于愿意听他说话了。他往前又踏了一步,双手紧紧抓着窗台,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急切地想将心中积郁的话全部倾泻而出。
「晚晚,我就知道妳还是在乎我的!」他的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欣喜与狂热,「妳那个夫君,他能给妳什么?他整天就知道看那些破书,哪有我懂妳?我这几天去了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找到了那个当年我们一起埋下的时间小盒!」
「晚晚,妳等我一下!」他说着,竟像是献宝一样,转身就往外跑,那股子冲劲和孩童般的急切,与记忆中那个调皮的少年重叠在了一起。然而,他没有看到,在他转身的瞬间,宋听晚脸上那抹温柔的微笑,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的淡漠。
「我不需要那些,我有夫君了,你也别再来找我了。」
那清冷却坚定的声音,像一盆冰水,兜头浇熄了许皓恩眼中燃起的火焰。他刚迈出的脚步猛地僵在原地,不可置信地回过头。他看到宋听晚依旧坐在窗边,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在她身上,她的表情却比寒冬的冰霜还要冷。那双曾经会因为他一句玩笑话而泛起涟漪的眼眸,此刻里面只有一片死寂的疏离。
「晚晚……妳……妳说什么?」许皓恩的声音干涩,像是被砂纸磨过。他无法理解,不愿相信。刚刚那抹微笑明明还在他脑海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最伤人的利刃。他紧紧抓着怀里那个冰冷的小木盒,那是他唯一的希望,此刻却烫得他几乎要拿不住。
她没有再重复,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眼神里没有恨,没有怨,甚至没有不耐烦,只有一种彻底的、不留余地的隔绝。这种平静的拒绝,远比任何激烈的斥责都更令人心碎。许皓恩觉得自己的心脏一寸寸冷了下去,血液都好像凝固了。
「为什么……」他喃喃自语,像是问她,又像是问自己,「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他想起了小时候在后山的约定,想起了她为他挡下蜂窝时坚毅的脸庞。可那些记忆,在此刻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他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终于,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
他嘴角的弧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冰冷的笑意。那笑意未达眼底,反而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就在此时,府内另一头突然传来一声瓷器碎裂的巨响,紧接着是仆人们一阵慌乱的惊呼。管家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了过去,立刻带着几个亲信匆匆赶去查看情况。
就是这一眨眼的工夫,许皓恩动了。他的快得惊人,像一道闪电般扑到窗前,根本不给宋听晚任何反应的机会。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麻袋从他宽大的衣袍下拿出,兜头盖下,世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与粗糙的布料摩擦中。她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尖叫,后颈便传来一阵剧痛,意识随即被无边的黑暗吞没。
他将她轻而易举地扛在肩上,那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镇定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趁着院中混乱,仆人们都奔向声音源头的空档,大步流星地从旁门离开。他的步伐平稳,表情自然,就像是来访的普通客人告辞一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谁也想不到,那位温文尔雅的少夫人,就这样被当成一袋无关紧要的货物,被光明正大地扛出了裴府的大门。
直到傍晚,晚霞将天空染成一片绚丽的橘红,裴净宥处理完翰林院的公务,带着一身温和的笑意回到院中,准备像往常一样看见他那安静的妻子时,却只发现空无一人的庭院,和那扇被晚风吹得轻轻晃动的窗。他心中的不安,在那一刻,疯狂地滋长起来。
当她恢复意识时,首先感受到的是身下传来的冰冷与粗糙,混合著浓重的霉味和干草的气息。她艰难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破旧不堪的茅屋里,昏暗的光线从墙壁的缝隙中透进来,勾勒出空气中飞舞的尘埃。许皓恩就站在不远处,脸上再没有之前的狂热,只剩一片死寂的阴郁。
她下意识地往后缩,直到后背抵住冰冷粗糙的土墙,才惊恐地看着他。她不知道他想做什么,这种未知的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掐住了她的心脏,让她几乎无法呼吸。从小到大对男人的害怕,在此刻被无限放大,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妳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可怕,像是在砂砾上滚动。「我找了妳那么多年,我以为……我以为妳也在等我。」他一步步朝她走近,眼神里是化不开的痛苦与执拗,每一步都像踩在她紧绷的神经上。
「裴净宥那种人,根本不配得到妳!」他突然低吼起来,蹲下身,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力道大得惊人。「晚晚,妳看着我,妳忘了吗?忘了后山的鸟窝,忘了河边的鱼,忘了妳说过会永远跟我在一起的吗?」他激动地摇晃着她,试图从她惊恐的眼神里,找到一丝过往的温情。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摇着头,那动作急切又凄凉,散乱的发丝拂过他冰冷的手指。她要他忘了,要他忘了那些早已过去的童年,要他忘了她,也放过他自己。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哀求,那不是回忆的温情,而是纯粹的、对眼前这个陌生男人的恐惧。
「忘了?」许皓恩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抓着她肩膀的手收得更紧,几乎要将她的骨头捏碎。他的脸因为极度的情绪而扭曲,看起来有些狰狞。「妳说忘了?妳怎么能说忘了!那是我们的一切!」他的声音拔高,在这间狭小的茅屋里回荡,带着令人心悸的疯狂。
「妳怕我?」他忽然注意到了她颤抖的身体和躲闪的眼神,这个发现让他眼中的痛苦迅速被一种屈辱的愤怒所取代。「妳在怕我?晚晚,妳竟然在怕我?!」他松开手,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后退一步,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记忆里那个会跟在他身后,满眼都是他的女孩,怎么会怕他?
「都是裴净宥……都是他!」他猛地转过身,一拳狠狠砸在墙上,扬起一片尘土。他猩红着眼转过头,死死地盯住蜷缩在角落的她。「是他把妳变成了这样!是他把妳从我身边抢走的!妳等着,我会让他付出代价,我会让他知道,妳从一开始就应该是我的!」
他眼中的疯狂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深色瓷瓶,拔开软木塞,一股浓烈又甜腻的异香瞬间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他晃了晃瓶子,低沉地说:「这是西域来的好东西,再烈的马用了都会变得温顺,何况是女人。」那话语里的轻蔑与决绝,让她的血液都冻结了。
恐惧像一张大网将她牢牢罩住,她连滚带爬地往后退,背部却死死抵住粗粝的土墙,退无可退。她惊恐地看着他一步步逼近,那双眼睛里再也没有一丝从前的温存,只剩下占有欲的火焰。许皓恩几乎是瞬间就欺身上前,粗糙的大手毫不留情地抓住她的衣裙,只听「刺啦」一声,布料应声而裂,露出她惊慌失措下微微颤抖的娇躯。
「别怕,很快妳就不会再怕了,妳只会求着我。」他轻笑着,声音嘶哑。他毫不犹豫地将她双腿强行分开,那清幽私密的花径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他眼前。她拼命地挣扎,却只是徒劳。下一刻,冰凉黏腻的液体顺着瓶口滴落,直接落在她那温热敏感的穴口上,激起她一阵战栗。
精油迅速渗入肌肤,一股奇异的燥热从腿心最深处猛地窜起,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发软,意识也变得模糊起来,那股让她窒息的恐惧似乎正在被一股陌生的、羞耻的渴求所取代。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身体开始泛起不正常的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