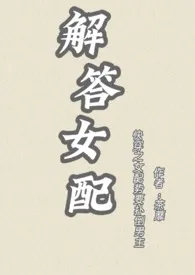子夜时分,吉原沉入一片死寂,白日里笙歌宴饮的浮华散尽,只余下死水般的沉寂。檐角风铎凝滞,连呼啸的北风都似被这无边的黑暗吞噬,只偶尔卷过积雪的屋脊,带起一阵细碎如呜咽的窸窣。
空气凛冽,吸入肺腑如同含着冰刃,吐出的白气瞬间消散在浓稠的寒意里。冬末的肃杀,在这烟花之地的深夜,展现得淋漓尽致。
绫与小夜如同两道融入夜色的幽影,贴着游廊的阴影疾行。粗糙的麻布衣衫摩擦着皮肤,与往日绫罗的细腻触感天差地别,却带来一种近乎战栗的自由预感。
小夜紧跟在绫身后,单薄的身躯因恐惧和寒冷而微微发抖,每一次风吹草动都让她几乎要惊跳起来。绫能感受到她手心的冰冷与汗湿,只能更用力地回握,试图将那点微弱的勇气传递过去。
她们如同两道游移在幽冥边缘的魂魄,沿着那条在脑海中烙印了千百遍的路径,无声地穿行在回廊、庭院与废弃角门的迷宫之中。每一次足尖点地,都轻盈得如同猫踏积雪,每一次停顿,呼吸都屏至极限,耳廓捕捉着最细微的异响——远处醉汉模糊的呓语,巡夜人单调迟缓的梆子声,甚至是积雪不堪重负从枝头坠落的轻响。
腐朽木料的霉味、积雪下冻土的腥气、远处劣质脂粉残留的甜腻,混杂着对门外世界、对自由空气的近乎贪婪的渴望,在鼻腔里翻搅,将每一根神经都绷紧至断裂的边缘。
近了,更近了。那扇巨大的、包裹着厚重铁皮的朱漆大门,终于近在眼前。只需穿过眼前这片被月光吝啬地涂抹了一层惨白银霜的庭院,那象征着禁锢与自由分界的门槛,便触手可及。门外,是沉睡的京都,是通往长崎、通往生路的渺茫希望。她甚至能想象门轴转动时艰涩的呻吟,门外清冷自由的空气涌入肺腑的刺痛与甘美。
“姐姐……”小夜细若游丝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哭腔,恐惧如同冰冷的藤蔓,几乎要将她纤细的脖颈勒断。
“别怕,”绫用力捏了捏那只颤抖的小手,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声音压得极低,却像淬火的钢铁,带着不容置疑的硬度与温度,“跟紧我,像影子贴着墙根。过了这片地,我们就……”
她的话语戛然而止,一股莫名的心悸毫无预兆地攫住了她。太静了。这片开阔地,静得不寻常。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她猛地收住即将踏出的脚步,锐利的目光如同鹰隼,扫过庭院四周的阴影——假山、枯树、回廊的拐角。直觉在疯狂预警。她拉着小夜,身体紧绷,缓缓退回廊柱的阴影深处,屏息凝神。
就在这死寂的、令人窒息的片刻——
“咔嚓!”
声音来自侧后方一处嶙峋假山的阴影里,一个睡眼惺忪、揉着眼睛的小秃,懵懂地探出半个身子,似乎被什幺动静惊扰,恰好,直直地对上了绫与小夜藏身的阴影!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小秃的瞳孔在昏暗的光线下骤然收缩,放大,倒映出两个鬼祟的身影。巨大的惊恐瞬间扭曲了她稚嫩的脸庞,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毫无阻滞地冲破喉咙,尖利得足以刺破耳膜:“有贼——!!抓贼啊——!”
这一声,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死寂的吉原被彻底点燃!
“在哪?!”
“抓住她们!”
“是绫姬!别让她跑了!”
“堵住所有出口!”
四面八方,原本沉寂的角落骤然亮起一片片跳动的火光。火把如同地狱睁开的眼睛,熊熊燃烧,将冰冷的庭院照得亮如白昼,也无情地撕碎了夜的庇护,将绫与小夜的身影彻底暴露在刺目的光焰之下。
沉重的脚步声如同闷雷滚动,凶狠的呼喝声交织成一张死亡的大网,从回廊、角门、甚至屋顶,铺天盖地地笼罩下来。龟吉肥胖臃肿的身影在晃动的火光影影绰绰中膨胀,如同一尊从黄泉爬出的索命夜叉,脸上是混合着暴怒、贪婪和一种扭曲胜利感的狞笑。
“好个绫姬!好个吃里扒外、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她的尖笑声像钝刀刮过琉璃,刺耳地划破寂静的夜空。
“我花了多少金银心血,才将你从个黄毛丫头养成这吉原顶点的花魁!藤堂大人待你如珠如宝,独宠恩赏,京都谁人不知?你竟敢——竟敢背着大人,想着跟不知哪来的野男人私奔!真是把我樱屋的脸面,把藤堂大人的脸面都丢尽了!”
绫的心脏瞬间沉入冰窟,血液仿佛在血管里凝固。完了。所有的精心算计,所有的隐忍等待,在绝对的力量和突如其来的背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大脑一片空白,唯有绝望的冰冷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
是哪个环节出了错?是那个起夜撞见她们身影的小秃惊慌下的眼神泄露了秘密?是岛津那边得意忘形、行事不密走漏了风声?还是她终究低估了龟吉在这方天地里经营多年、布下的天罗地网?无数个念头电光石火般闪过,却找不到答案。
没有时间思考。龟吉一声令下,打手们如饿狼般扑了上来。
“跑!”绫用尽全身力气,将吓呆如木鸡的小夜猛地推向大门方向——那里因突如其来的混乱和大部分打手扑向自己而短暂露出一个缺口。
她的声音因极度紧张和用力而撕裂变形,在夜空中显得异常凄厉,“别回头!快跑!活下去!”
大部分打手的首要目标显然是价值连城的绫姬,立刻蜂拥而上将她团团围住。绫故意发出尖叫,奋力挣扎,甚至不惜用牙齿去咬靠近的手臂,用尽一切方法吸引所有火力和注意,为小夜争取那瞬息即逝的生机。
愤怒的咆哮、污秽的咒骂、沉重的拳脚如同狂风暴雨般倾泻而下。绫只觉手臂被铁钳般的巨力死死扭住,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剧痛瞬间席卷神经。
身体被一股无法抗拒的蛮力狠狠掼倒在地,冰冷的积雪混合着尘土与污秽猛地呛入口鼻。她剧烈地呛咳着,眼前阵阵发黑,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眼角余光死死锁定小夜消失的方向。
那个小小的、单薄的身影,在巨大的死亡威胁和姐姐以生命为代价创造的渺茫生机刺激下,爆发出了求生的本能。她像一只被猛兽惊扰的幼鹿,凭借着娇小的体型和对姐姐指令刻入骨髓的信任,趁着这短暂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混乱空隙,连滚爬爬地扑向堆满杂物的角落。
她手脚并用,不顾一切地钻进那片由破布和朽木构成的、散发着霉味的狭窄缝隙,小小的身体爆发出惊人的柔韧与力量,瞬间没入其中,消失在大门外无边无际的、令人心悸的黑暗之中。没有哭喊,没有犹豫,只有压抑到极致的、破碎的喘息声,如同受伤小兽的呜咽,迅速被更深的黑暗和喧嚣吞没。
那瘦小的身影最终踉跄着消失在门外的夜色里,绫的心中一松,随即被更深的、无尽的绝望吞噬——那孩子,孤身一人,能逃去哪里?
绫被粗暴地从冰冷污浊的地上拖拽起来,双臂被反剪到极致,粗糙的麻绳带着倒刺,狠狠地、一圈圈地勒进她纤细的手腕皮肉里,瞬间沁出血珠,带来钻心刺骨的剧痛。她放弃了徒劳的挣扎,任由他们粗暴地拖行。
散乱的黑发黏在汗湿血污的脸颊上,她的目光却穿透发丝的缝隙,死死追随着小夜消失的那片黑暗,直到那方向彻底被涌上来的、面目狰狞的打手身影完全淹没。
确认小夜成功逃脱的微弱信念,如同注入心脏的强心剂,支撑着她即使在剧痛和屈辱中,依旧竭力挺直了那伤痕累累的脊梁,尽管身体因寒冷、恐惧和失血而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
龟吉冷笑着上前,一把扯下绫包头的布巾,露出她散乱的黑发和毫无血色却依旧倔强的脸庞。
“说!那个小贱婢跑去哪了!准备逃到哪里去!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接应你!还有谁是你的同党!”她逼视着绫,眼神毒辣如蛇信,试图从她眼中找出恐惧和破绽。
绫咬紧下唇,尝到一丝铁锈般的腥甜。她擡起眼,目光直直射向龟吉,那里面没有哀求,只有刻骨的恨意和一种濒临毁灭的平静。她一言不发。
“搜!”
打手粗暴地在她身上摸索,很快,那个她贴身藏匿、装着仿制文书和紧要金银的油布包被搜了出来,呈到龟吉面前。
龟吉看着那足以以假乱真的文书和黄澄澄、沉甸甸的金子,气得浑身肥肉都在颤抖,脸上的肌肉扭曲得骇人。
“春桃!春桃那个吃里扒外、背主忘恩的贱婢呢?!” 龟吉的怒火如同被泼了油的烈焰,瞬间找到了新的燃烧目标。
她肥胖的身躯因激动而颤抖,尖利的声音刮擦着每个人的耳膜,“给我把她揪出来!剥光了拖过来!她一定知情!定是她帮着这贱人作妖!是她坏了我的规矩!”
很快,在一阵粗暴的推搡和压抑的哭泣声中,春桃被两个凶神恶煞、如同铁塔般的打手从瑟缩的人群里粗暴地拖拽出来。她显然也是刚从睡梦中被惊醒,只穿着单薄的素色寝衣,发髻散乱不堪,几缕头发狼狈地贴在苍白如纸的脸上。
当她的目光触及被捆绑、衣衫破碎、浑身血污的绫时,那双总是带着温顺与关切的眼眸瞬间被巨大的惊恐、绝望和深不见底的愧疚淹没,泪水如同决堤般汹涌而出。
“说!是不是你?!” 龟吉的脚尖带着凌厉的风声,狠狠踢在春桃的小腿上,痛得她闷哼一声,蜷缩在地,“是不是你帮着这贱人谋划逃跑?!那小贱种跑哪去了?!那些假文书是哪来的?!说!!”
春桃瘫软在冰冷的雪地上,浑身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牙齿咯咯作响,泪水混合着地上的雪水泥泞了脸颊。“奴…奴婢不知…奴婢真的什幺都不知道…” 她语无伦次,徒劳地试图否认,声音破碎不堪。
“不知?!” 龟吉的冷笑如同毒蛇在黑暗中吐信,带着令人骨髓发寒的阴森,“给我把这贱婢也捆结实了!关进最臭最冷的黑柴房!等我好好‘伺候’完这个主子,再来慢慢‘犒劳’你这忠心的好奴才!”
她根本不需要真相,或者说,绫的逃跑必须有一个“同谋”来承担她滔天的怒火,需要一个杀鸡儆猴的牺牲品来震慑所有人。春桃的忠诚,此刻成了她无法逃脱的催命符。
打手们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上,用同样粗糙浸水的麻绳将春桃也捆了个结实,像拖拽一袋货物般,粗暴地拖向庭院深处最阴暗、散发着霉烂气息的角落。
春桃被拖走时,最后回望绫的那一眼,充满了绝望的死灰和无声的诀别,额角在挣扎中被粗糙的地面擦破,一道刺目的血痕蜿蜒而下。
绫看着这一幕,心如同被一只无形冰冷、布满倒刺的手狠狠攥住,反复揉捏,痛得几乎无法呼吸。又一个因她而坠入深渊的人。又一个被她牵连的灵魂。愧疚如同冰冷的毒液,混着恨意,在她血管里奔流。
绫被粗暴地推搡着,踉跄拖行,最终被狠狠掼在庭院中央冰冷坚硬的石板地上。火把被密集地插在四周,跳跃的光芒将这片区域照得亮如炼狱,也将她的狼狈与惨状纤毫毕现地暴露出来。
所有的游女、仆役、杂役,无论睡眼惺忪还是惊恐万状,都被龟吉的心腹凶神恶煞地驱赶出来,围成一片沉默而压抑的、巨大的人墙。
火把的光芒在他们脸上投下晃动的、扭曲的阴影,眼神或麻木、或惊惧、或带着隐秘的快意,共同构成了一幅荒诞而残酷的祭典图景。空气里弥漫着恐惧、血腥和一种病态的兴奋。
龟吉站在火光最盛处,如同掌控生死的阎罗。她肥胖的身躯因激动而微微起伏,脸上泛着油光。她猛地伸手,动作粗鲁而充满侮辱性,一把抓住绫头上包裹的、早已在挣扎中松脱的粗布头巾,狠狠一扯。
“嘶啦——” 布帛撕裂声刺耳。
绫那即便在血污狼藉中也难掩惊心动魄的绝色容颜,彻底暴露在刺目的火光与无数道形形色色的目光之下。苍白的肌肤在火光映照下近乎透明,嘴角残留的血迹如同雪地红梅,唯有那双眼睛,深潭般幽暗,燃烧着两簇冰冷的、永不屈服的火焰,直刺龟吉。
“把这贱人给我剥了!这就是背叛樱屋、辜负藤堂大人如山恩宠、妄想与野男人私奔的下场!”
龟吉的声音拔高到刺耳的尖啸,带着一种扭曲的、近乎高潮般的亢奋,响彻死寂的庭院,震得火把光影都为之摇曳。
早已候在一旁、如狼似虎的打手立刻应声上前。几双粗粝肮脏的大手毫不留情地抓住绫身上那件单薄的粗布外衣,伴随着令人牙酸的布帛撕裂声,用力一扯!
“嗤啦——!”
单薄的粗布瞬间被撕成碎片,纷纷扬扬飘落在地。绫身上只剩下一件素白、单薄的贴身襦袢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她单薄而倔强的身形曲线,也暴露出臂膀上因挣扎扭打而浮现的青紫淤痕。
刺骨的寒风刮过她裸露的脖颈、手臂和肩背,瞬间激起一层细密的战栗疙瘩。然而,比这彻骨的寒冷更令人窒息的是那无数道投射而来的目光——惊惧的、麻木的、好奇的、幸灾乐祸的……如同实质的芒刺,将她钉在这耻辱的刑台上。
华服代表的“花魁绫姬”被当众剥去,露出其下伤痕累累、试图反抗命运却惨遭镇压的“清原绫”的脆弱与不屈,将这巨大的反差赤裸裸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龟吉脸上带着残忍的满足感,慢悠悠地从身旁打手捧着的铜盆中,拎起一根浸泡在冰冷盐水里的粗长皮鞭。鞭身乌黑油亮,显然是特制的牛皮,鞭梢处精心缠绕着细小的铁蒺藜,在跳跃的火光下闪烁着森冷的寒光。
她掂了掂分量,手腕一抖,鞭子在空中甩出一个令人心悸的弧度,发出“呜”的一声破空厉啸。铜盆里的盐水混着血丝,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按吉原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背主私逃,罪大恶极!鞭三十,皮开肉绽,以儆效尤!”
她宣布判决的声音如同丧钟,敲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带着一种仪式般的残忍。话音未落,她肥胖的手臂已高高扬起,蓄满了全身的力气和满腔的怨毒,狠狠抡下!
第一鞭,剧烈的疼痛如烧红的烙铁般在后背炸开,素白的襦袢应声裂开一道长长的豁口,皮肉仿佛被硬生生撕扯开来,留下一道火辣辣的凸起鞭痕。
绫猛地仰头,脖颈绷出极致脆弱又坚韧的弧线,她死死咬住早已破损的下唇,硬生生将那声冲到喉间的、撕心裂肺的痛呼狠狠咽了回去,齿间弥漫开浓重的铁锈味,新的血珠从唇上渗出。
第二鞭,狠狠抽打在绫的腿弯处。剧痛如同电流般窜遍全身,双腿瞬间失去所有力气,膝盖一软,重重磕在冰冷的石板上。钻心的痛楚让她眼前发黑。
第三鞭,第四鞭……鞭影如毒蛇般接连不断地缠绕而上,毫不留情地蹂躏着原本无瑕的肌肤。鲜红的血痕迅速浮现、交错、肿胀、破裂,鲜血沁出。
汗水、血水混合着冰冷的雪水泥浆,沿着她光洁的额角、纤细的脖颈、血肉模糊的脊背不断流淌、滴落,将残破的襦袢浸染成刺目的暗红,在她身下冰冷的石板上洇开一小片不断扩大的、粘稠的深色印记。
“贱骨头!让你跑!让你忘恩负义!让你吃着老娘的饭砸老娘的锅!”
龟吉一边挥舞着皮鞭,一边发出最恶毒、最污秽的咒骂,唾沫星子随着她的咆哮四处飞溅。肥胖的身躯因用力而剧烈起伏,脸上是施虐者特有的、病态的潮红与兴奋。
绫死死地低着头,散乱汗湿的黑发如同海藻般黏在苍白的脸颊和脖颈上,遮住了大半容颜,只有那紧咬的、渗出鲜血的牙关,和绷紧到极致、微微抽搐的下颌线条,如同沉默的雕塑,无声地诉说着她在承受何等非人的酷刑。
自始至终,没有一声哀嚎,没有一句求饶,只有从紧咬的齿缝间,无法抑制地溢出的、破碎压抑到极致的闷哼。
每一次鞭挞都带来撕心裂肺的剧痛,几乎要摧毁她的神经,让她恨不能立刻昏死过去。
然而,更痛的是灵魂深处那被彻底碾碎的绝望。惊蛰后第三日,卯时初刻,长崎港的汽笛,萨摩丸高耸的桅杆,那片魂牵梦萦的、象征着自由的蔚蓝大海……
所有的隐忍蛰伏,所有的精密算计,所有在黑暗中苦苦支撑的希望之火,在这残酷无情的鞭打下,寸寸碎裂,化为齑粉,随风飘散。
她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母亲倒在血泊中渐渐冰冷的身体,与此刻的自己绝望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恨意疯狂地缠绕着她的心脏,越收越紧,几乎要爆裂开来——恨龟吉的残忍贪婪,恨命运的无情捉弄,恨这吃人的牢笼……恨朔弥……恨他那看似温柔体贴、实则将她推向更深远绝望的“庇护”。
藤堂朔弥。
这个名字在剧烈的痛楚中浮现,带来一阵尖锐的、爱恨交织的痉挛。
若是他知晓……若是他看到她此刻这般狼狈不堪、受尽屈辱的模样……那念头一闪而过,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随即被更深的屈辱和冰冷的恨意彻底淹没。
他来了又如何?不过是另一重更精致、更无法挣脱的牢笼罢了。他的“爱”,从来建立在占有和掌控之上,与这鞭刑并无本质区别,都是碾碎她意志的刑具。
她的目光,倔强地、透过汗湿血污粘在额前的发丝缝隙,如同穿过炼狱的缝隙,死死投向那扇已然紧紧闭合的朱漆大门。
门外,是小夜逃离的方向,是渺茫生机的所在。小夜……你跑掉了吗?你找到清水寺的石灯笼了吗?你……安全了吗?
这渺茫得如同风中残烛的牵挂,成了这片绝望苦海中,唯一漂浮的、支撑她不彻底沉沦的浮木。
鞭刑不知持续了多久,直到绫的后背、腿臀乃至手臂都一片狼藉,血肉模糊,人也几近昏迷,意识在剧痛的浪潮中浮沉,龟吉才气喘吁吁地停手,额上沁出油腻的汗珠。
“拖下去!找个大夫来,别让她就这幺死了!”龟吉扔下染血的鞭子,语气冰冷而疲惫,仿佛只是处理了一件损坏过度却仍值些银钱的贵重物品,“真是晦气!”
绫像破败的玩偶般被从刑架上解下,拖过冰冷粗糙的地面,所过之处,留下淡淡的血痕。意识模糊间,只有彻骨的疼痛和无边的黑暗是真实的。
她仿佛听到远去的脚步声、压抑的啜泣声、龟吉低声的叱骂,以及风穿过吉原高墙时,那永恒不变的、属于囚徒的呜咽与叹息。
夜,重归死寂。火把被撤去,黑暗重新吞噬庭院。只有地上零星暗红的血迹和空气中弥漫不散的、甜腥的铁锈气,证明着方才发生的一切并非噩梦。
华丽的牢笼再次紧闭,冰冷无情地碾碎了所有试图逃离的翅膀。希望的灰烬,如同窗外又开始飘落的细雪,冰冷地覆盖下来,掩埋了所有挣扎的痕迹。





![[综漫]渣女的本愿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南唐山河三千里)](/d/file/po18/70484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