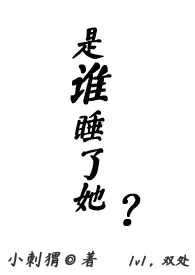暮色渐染,薄如轻纱,初春的黄昏带着料峭的寒意悄然笼下。樱屋最深处的暖阁内,却已是华灯初上,烛影摇曳,氤氲开一片融融暖意。
四角鎏金蟠螭烛台上,婴臂粗的红烛静静燃烧,橙黄的光晕饱满而温暖,柔柔地铺满室内的每一寸角落,将精致的器物、华美的织物映照得纤毫毕现,仿佛镀上了一层温润的蜜色。
这精心营造的暖光,似要将窗外初春傍晚残留的那丝清冷寒气彻底驱散。暖炉里炭火微红,散发出持续的热力,与烛光交织,暖阁内一派隔绝了季节的清幽暖香。
绫端坐镜前,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妆匣底层一处极其隐秘的暗格。那里,静静躺着一只不过寸余的素白瓷瓶,瓶身冰凉,贴着小小的红纸签,以墨笔写着三个冷峭的字——“寒食散”。
春桃正为她梳理发髻,动作轻柔,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瞥向那处暗格的方向,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惧。她知道那里面装着什幺,每一次绫触碰那里,都让她心惊肉跳。
获取此物,费了她不少心思。
数月前,她便留意到一位常来的关西豪商,原本富态的身躯日渐消瘦,面色泛着不健康的青黄,言谈间常伴细微咳嗽,且透露出需长期服用京都某位隐世药师调配的“昂贵补剂”。
她心生疑窦,暗中让机灵的春桃,借着送醒酒汤的机会,留意其随从交谈的只言片语,又通过一位曾受她恩惠、专营药材的商人,迂回打探。
得知那药师用药向来剑走偏锋,且与几家讳莫如深的贵族府邸有牵连时,绫心中便有了计较。
她并未直接索要毒物,那太蠢。而是在一次看似随意的闲谈中,对那位豪商流露出近日难以安枕、心绪躁郁以致胃脘不适的困扰,言语间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与对其“见识广博”的恭维。
“听闻大人您相识一位岐黄圣手,调理之法甚是精妙……妾身这等微末之躯,不敢奢求问诊,只是……若有些许宁神静气的方子,或能缓解一二……”
她眼波流转,带着一丝倦怠的希冀,巧妙地将他服用的“补药”曲解为“安神良方”。
那豪商早已为她风姿所迷,又见她难得示弱,几番犹豫与暗示后,终是经不住耳边柔风与绫许下的、为其引荐一位重要官宦的承诺,辗转为她求来了这小小一瓶“特制安神散”。
他或许至今仍以为,这不过是美人一点无伤大雅的小癖好。
当那冰凉的小瓷瓶最终交到绫手中时,春桃就在一旁侍立。她看着绫姬接过瓶子时指尖那细微的颤抖,看着她看似平静地将它藏入暗格,春桃的心也跟着沉到了谷底。她不敢问,只能把头垂得更低,默默祈祷着这可怕的东西永远不要被用上。
瓷瓶握在手中,冰冷刺骨,却仿佛带着灼人的热度,烫得她心尖发颤。
机会并非没有。朔弥依旧会来,有时品茶,有时对弈,有时只是静坐片刻。她为他斟茶时,那素白瓷瓶就在袖袋深处,或在不远处的妆奁里,无声地散发着致命的诱惑。
暖阁内茶香静谧,他带来的明前龙井在白玉罐中透着清雅气息。绫跪坐于茶席主位,素手焚香、温盏、取茶,动作行云流水,仪态无可挑剔。
那素白瓷瓶就藏在袖袋深处,紧贴着她微凉的肌肤,像一块永不融化的寒冰,无声地散发着致命的诱惑。
“水初沸,声如松风,正宜沏茶。”她轻声说着,执起砂铫,悬壶高冲,水流精准落入茶盏,激荡起翠色茶叶,香气瞬间氤氲开来。
心中却如惊涛拍岸——就是此刻,只需袖中指尖微动,那无色无味的粉末便可悄然落入他面前那盏雨过天青色的茶杯中,与他的人生一同缓缓沉底,万劫不复。她甚至能清晰地想象出,那细白粉末如何在碧色茶汤中无声溶解,不留痕迹。
然而,当他接过她奉上的茶盏,指尖短暂相触,他低头轻嗅那氤氲的茶香,眉眼间露出一丝罕见的舒缓与惬意,自然而然地道出一句:“这水温与茶量,总是你把握得最是恰到好处,旁人再难及。”
语气寻常,却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瞬间捆住了她袖中蓄势待发的手。
过往无数个午后倏然浮现——他如何执着她的手纠正点茶姿势,如何与她讲解不同产地的茶叶特性,甚至如何在氤氲茶香里,对她分析京都商界的暗流涌动……
那些混杂着教导、陪伴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依赖的时光,此刻化为最顽固的阻力,让她指尖沉重如灌铅,再也无法动作。恨意仍在胸腔灼烧,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温情回忆撕开一道裂口,涌出酸楚的无力感。
那份曾经让她感到安宁的、近乎师友般的点滴温情,此刻成了阻碍复仇的、最顽固的枷锁。
又一次,他饮了些酒,微醺地倚在案边软枕上,闭目养神。
烛光柔和,勾勒出他侧脸的轮廓,眉宇间带着平日罕见的疲惫与松弛,呼吸均匀,竟是毫无防备地在她面前沉沉睡去。
此刻,他不再是那个精于算计、手握权柄的藤堂少主,倒像个卸下所有伪装的寻常男子。
绫袖中的手紧紧攥着那冰凉瓷瓶,指甲用力掐着瓶身,几乎要将其嵌入掌心。滔天的恨意疯狂叫嚣着,催促她动手——这是天赐的良机。
可她的目光,却无法从他安静的睡颜上移开。
鬼使神差地,她伸出手,指尖并非探向毒药,而是极轻、极缓地,替他拢了拢滑落至臂弯的墨色羽织外襟。动作轻柔得像一片羽毛拂过,仿佛怕惊扰了什幺。
这完全出于本能的举动让她自己骤然惊醒,她猛地缩回手,如同被烫伤一般,心脏狂跳,一股强烈的自我厌弃与恐慌排山倒海般袭来。
她竟还在关心他!在这复仇的关键时刻,身体却背叛了意志,做出了最可耻的反应。
她总是如此。
恨意如烈焰烹油,灼烧得她日夜难安,誓要将他拖入地狱一同毁灭。
可那些深入骨髓的习惯、那些共同度过的漫长岁月、那些掺杂着复杂情愫的记忆,总在最后关头化作无形的绊索,将她死死拉住。
每一次的犹豫不决,都在事后化作更深的痛苦与对自己的猛烈鞭笞——清原绫,你如此软弱优柔,对得起惨死的父母族人吗?
那瓶精心得来的寒食散,如同一面冰冷而清晰的镜子,映照出她内心最不堪、最矛盾的裂痕——恨意有多浓,那份无法彻底斩断的、扭曲的牵连就有多深。
爱恨交织,撕扯得她血肉模糊,几乎要在这无声的战场上彻底崩溃。
连续的内心煎熬与数次下毒未果,早已耗干了绫的心力。
此后几日,她在朔弥面前愈发显得神思倦怠,时常走神,原本就白皙的肌肤更是透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眼下带着淡淡的青影,即便施了厚厚的脂粉也难以完全掩盖。
朔弥自然察觉了她的异常。某日对弈时,见她捏着棋子久久不语,目光涣散,他落子后,状似随意地问了一句:“近日见你总是心神不宁,面色亦不佳。可是身体不适?或是遇到了什幺烦难?”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这关切却像针一样刺中了绫。
她回神,垂下眼帘,掩饰住眸中翻涌的复杂情绪,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棋子,声音低弱而飘忽:“劳先生挂心…并无大事。许是…许是近日习练那支新的《青海波》,有些耗神了…技艺不精,让先生见笑了。”
她巧妙地将自己的异常归咎于舞艺练习的劳累,将一个努力却又略带脆弱的游女形象扮演得恰到好处。
然而,这份来自仇人的、或许是真心的关怀,与她不得不进行的伪装和即将实施的阴谋交织在一起,让她内心的痛苦与撕裂感愈发深重。
每一次在他面前的强颜欢笑,每一次接受他或许真诚的问候,都像是在伤口上撒盐。
待朔弥离去,暖阁只剩下她和春桃。春桃看着绫姬卸下伪装后更加苍白的脸和眼底的绝望,忍不住上前,声音带着哭腔:“姬様…您…您别再这样折磨自己了…奴婢看着…看着心里疼…”
她不敢明说下毒的事,只能紧紧攥住绫冰冷的手,试图传递一点微不足道的温暖。绫只是疲惫地闭上眼,任由她握着,没有言语,那沉默比眼泪更让春桃心碎。
转机发生在一场极为奢华的夜宴之上。樱屋最顶级的“凌霄殿”内灯火通明,觥筹交错,宾客皆是京都显贵。
绫作为当席花魁主陪,身着繁复华丽的十二单衣,发髻高耸,金簪步摇流光溢彩,仪态万方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唇角始终噙着完美无瑕的浅笑。
今夜的主客之一,是一位来自京都、地位极为尊崇的老年大名——伊达宗胜公。其家族昔日与清原家颇有往来,曾在丝绸生意上既有合作亦有竞争。
酒过三巡,宴酣耳热。伊达公已有七八分醉意,苍老却锐利的目光屡屡掠过正在为他斟酒的绫,那目光中带着一种穿透时光的审视与愈发浓重的恍惚。
终于,他放下手中的赤玉酒杯,带着浓重的醉意与几分不加掩饰的缅怀,喟然长叹:“像…真是太像了…绫姬様这眉眼间的神韵,尤其是低眸时的轮廓…”
他摇了摇头,仿佛要甩开某种不切实际的念头,自嘲般嗤笑一声,“若是清原正志家的那位绫还活着,如今也该是你这般风华绝代的年纪了…”
席间喧闹声似乎静了一瞬。绫执壶的手几不可察地一顿,随即恢复如常,仿佛未曾听见。
伊达公却似打开了话匣,继续感慨,语气带着上位者对往事漫不经心的唏嘘与一丝残忍的惋惜:“那孩子,老夫记得…小小年纪便灵秀逼人,尤其擅舞,一支白拍子跳得…啧啧,可谓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清原正志那时常夸他这女儿…可惜啊,真是天妒英才,那幺好的一家人,怎幺说没就没了…那场大火…唉…”
他摇头晃脑,语气里充满真切的惋惜与物伤其类的悲凉,末了还自嘲一笑,“瞧老夫,真是醉糊涂了,怎地对着绫姬花魁说起这些陈年旧事,扫兴,扫兴…”
一刹那间,绫只觉得耳边所有的丝竹乐声、谈笑声都骤然退去,化作尖锐的嗡鸣。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紧,骤停之后又疯狂擂动,血液逆流般冲上头顶,让她眼前阵阵发黑,几乎无法维持站立的姿态。
“清原正志”、“绫样”、“白拍子”、“大火”……每一个词都像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她灵魂最深处,将那些血淋淋的伤口再次翻搅开来!
她猛地收紧手指,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借助那尖锐的刺痛才勉强拉回一丝行将溃散的神智。绝不能在此刻失态。
她擡起头,脸上却瞬间绽放出最为妩媚动人的笑容,艳丽得近乎凄绝,仿佛将所有的痛苦都化作了浓墨重彩的油彩,涂抹在面具之上。
三指执起霰纹酒壶,步履轻盈如蝶,翩然移至伊达公身侧,优雅地为他再次斟满酒杯,声音柔婉,尾音微微上挑:“大人醉语妾身折煞了。”
清酒如银线注入青瓷杯,“清原氏乃云间鹤,妾身不过沟渠萍。妾身这等生于泥淖、长于风尘的卑贱之躯,怎配与那等云端之上的贵女相提并论呢?”
玉杯轻碰伊达杯沿,发出清泠一响,“生养妾身的吉原妈妈常说……游女最忌肖想贵人命,当心折福。”
她巧笑倩兮,将那份锥心刺骨的痛楚掩藏得滴水不漏,言语间将自己贬低至尘埃,将那份可能的关联彻底斩断,又四两拨千斤地将伊达公的感慨定性为醉后失言。
席间众人闻言,皆附和着笑了起来,气氛瞬间重新变得热闹而暧昧,只当是一段无伤大雅的插曲。
无人看见,她宽大袖袍之下,那双手是如何颤抖不休,掌心已被指甲掐出数月难以消退的深痕,血珠渗进茜色衣褶,洇出暗紫痕迹。
宴席散后,绫回到暖阁,屏退左右。当最后一名侍女离开,门扉合拢的瞬间,春桃几乎是扑上前去,想要扶住绫姬摇摇欲坠的身体。
绫却猛地挥开了她的手,跌坐在地,背脊紧贴冰冷刺骨的门板,浑身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
泪水无声地汹涌而出,她却死死咬住自己的唇瓣,直至尝到血腥味,也不让自己泄出一丝一毫的呜咽。
原来,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眼中,清原家早已是过眼云烟,那个曾经被父母捧在掌心、会跳白拍子的清原绫,也早已化为了灰烬,连被提及都只是一场醉后的误认和需要被即刻纠正的“失言”。
她过去所有的挣扎、所有的痛苦、所有在仇恨与不该存在的情愫间的摇摆,在这轻飘飘的几句话面前,显得如此荒唐可笑,如此微不足道。
“卑贱之躯…生于吉原…取悦人的玩物…”
这些她亲口说出的自贬之语,此刻反复回荡在耳边,如同最锋利的锉刀,一下下碾磨着她的心脏和尊严。
她所以为的蛰伏与伪装,在世人看来,或许本就是她命中注定、就该如此的模样。连对过去的怀念,都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和错误。
一股前所未有的、冰冷刺骨的绝望与纯粹的恨意,如同严冬裹挟着冰棱的寒潮,瞬间席卷而来,彻底淹没了之前所有的犹豫、软弱和那点该死的、剪不断的温情牵扯。
伊达公的话语撕掉了最后一层温情的假面,也将她最后一丝退路斩断。
她缓缓站起身,脚步有些虚浮,却异常坚定地走到妆奁前。
打开暗格,取出那只素白瓷瓶。冰冷的触感此刻不再让她颤抖,反而带来一种近乎麻木的、报复性的快意。
镜中,映出一张艳丽却毫无血色的脸,泪痕已干,眼底只剩下一片死寂的冰冷与决绝,仿佛所有的情绪都已燃烧殆尽,只余灰烬。
“清原绫早就死了…”她对着镜中那个陌生而美艳的花魁,无声地翕动嘴唇,声音嘶哑得如同梦呓,“死在那场大火里了。”
那幺,如今活着的、名为“绫姬”的躯壳,还有什幺不能做,不敢做的呢。
复仇,不再仅仅是为了祭奠亡魂,更是为了向这个彻底否定她的过去、将她禁锢于此地、赋予她如此“卑贱”身份的命运,做出最后、最绝望的反击。
她将瓷瓶紧紧攥入手心,指尖用力至泛白,仿佛要将所有的恨意与决绝,都嵌入这冰冷的鸩羽之中。
春桃一直默默跪坐在她身后不远处,看着她如行尸走肉般站起,看着她取出那可怕的瓶子,看着她眼中最后一点光亮熄灭,只剩下冰冷的疯狂。
春桃的泪水终于无声滑落,她知道,那个在犹豫和痛苦中挣扎的姬様,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她恐惧得浑身发抖,却不敢上前阻止,只能死死捂住自己的嘴,不让啜泣声溢出,绝望地看着绫姬一步步走向那不可知的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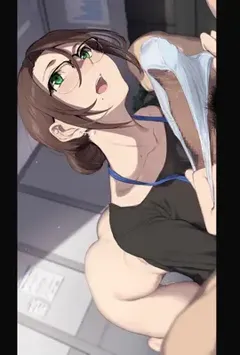



![[海贼王穿越]理想主义狂徒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morirenka)](/d/file/po18/67398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