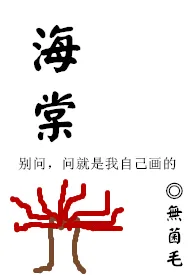二十二岁的深秋,霜风已然染红了樱屋庭院里几株老枫,炽烈如血,与廊下渐次点亮的暖融灯火形成鲜明对照。时光悄然在绫身上刻下痕迹,非是容颜衰老,而是一种淬炼后的清冽与沉静。
两年余的光阴,足以将一块璞玉打磨得光华灼灼,亦能将一颗心淬炼得坚冷如铁。暖阁的灯火,见证过无数个枯坐到天明的夜晚。
绫指尖的茧,生了又破,破了再生,直至抚过最光滑的丝绸也能感受到那层坚硬的厚度。
三味线的曲谱烂熟于心,每一个音符都灌注了无人知晓的孤寂与恨意;茶道的仪轨刻入骨髓,一举一动皆可入画,却鲜有人知她曾因练习一个“乱れ手”手法直至手腕肿痛难擡;和歌的底蕴在无数卷古籍中沉淀,字句间的哀愁与锐利,皆是她心境的映射。
她的声名,并非凭空而来。那是用近乎自虐的勤勉、滴水不漏的周旋、以及那份日益淬炼出的、既令人倾倒又难以亵玩的气度,一寸寸挣来的。
京都的风月场与上层社交圈中,“樱屋の绫姬”已成为一个象征。她的茶席一位难求,她的琴音被赞有“孤鹤唳霜”之清越,她的才情与应对,令无数公卿文人、豪商巨贾折服。
这份声名,非凭空而来,亦非仅系于藤堂朔弥的荫蔽。“樱屋の绫姬”之名,如同深秋最耀眼的枫霞,在京都上层圈层中灼灼盛放。几位极为显赫的常连恩客,不遗余力地为她造势。
关西的盐业巨擘佐藤包下樱屋“观月亭”整整三日,广发请帖,名为赏菊,实则为绫姬搭建展示才艺的璀璨舞台;
一位退隐的博学老公卿细川,在品评她所作和歌后,击节赞叹,称其“有王朝遗韵”,并赠予一套珍贵的古抄本《万叶集》;
更有豪客一掷千金,搜罗来前朝失传的名琴“秋涧”,只为博她奏响一曲。
这些支持喧嚣而高调,源于对她本人才华气度的真心欣赏与投资,他们或许隐约知晓藤堂朔弥的存在,却更愿将这视为美人间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而非她价值的唯一依凭。
朔弥的身影,依旧定期出现在暖阁。他的支持变得更为隐秘而高效。他不再点评她的琴艺,而是带来失传的乐谱孤本;不再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只是某位曾对绫出言不逊的客人,其家族生意会悄然遇到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他自身举办的顶级商会宴席,绫开始以“特邀”的身份列席,并非作为女伴,而是以精湛的茶道或琴艺为宴席增色,这本身便是无声的背书。
他仿佛一位耐心的投资者,冷静地看着自己珍视的藏品价值攀升,并提供着恰到好处的养护。
偶尔,在茶香氤氲间,他会凝视她越发清冷坚毅的侧脸,心中掠过一丝复杂的激赏与难以言喻的怅惘。她愈发光彩夺目,离他似乎也更远了些。
朔弥的支持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让绫在利用其资源时,那份自我厌恶与屈辱感如影随形。
每次独处,他眼中纯粹的欣赏让她胃部痉挛。当他不带狎昵的关切传来,过往那些生辰惊喜的记忆便不受控地翻涌。这时她总会咬住口腔内壁,用血腥味压下心软,指甲深陷掌心直到刺痛——恨自己竟对仇人残留温情。
龟吉精明的眼中早已精光四射。流水般的“扬代”和与日俱增的声望,让绫姬成为樱屋当之无愧的瑰宝与摇钱树。他摩拳擦掌,只待一个足以服众、光芒万丈的契机,为这棵摇钱树正式加冕“花魁”之名。
契机伴随着风险而来。一位以性情乖戾、刻薄挑剔闻名的亲王宠臣——近卫中将高仓显时,奉亲王之命巡视京都,竟点名要樱屋绫姬侍宴。
消息传来,樱屋上下如临大敌。此人性情阴晴不定,稍有不满,便能令人身败名裂。这无疑是对绫姬“格”与“气度”的终极考验,亦是加冕前最后、也最险峻的一道门槛。
宴设于樱屋最顶级的“天星阁”。金屏玉箔,烛火通明,映照着满室华贵与无形压力。
高仓显时端坐主位,面容冷峻,眼神如鹰隼般锐利扫视。绫身着素雅不失庄重的淡青色吴服,墨发仅以一支素玉簪绾定,脂粉淡扫,缓步入席,姿态沉静如深潭古水。
绫素手执古窑茶盏,恭敬奉上。高仓显时指尖“无意”一碰,滚烫的茶汤连同名贵的茶盏瞬间倾覆,泼溅在绫素雅的衣摆上,晕开深褐污迹,热气蒸腾。
满座皆惊。绫却连眉梢都未曾动一下。她只是极轻地后退半步,避开继续流淌的水渍,随即深深俯身:“大人受惊了。是妾身不慎。”声音平稳无波。
她示意侍女上前清理,自己则姿态优雅地告退,不过片刻,便换上一套同样素净的藕色衣衫返回,从容续上茶水,仿佛方才的插曲从未发生。宠臣冷眼瞧着,鼻中几不可闻地轻哼一声。
席间论及汉诗,高仓显时故意曲解一首冷僻的边塞诗,语带讥诮地向绫发难。:“‘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此等悲戚,不过妇人无谓之思。大丈夫当死于边野,何须闺阁垂泪?绫姬以为如何?”
绫垂眸聆听,待他说完,才微微欠身,声音清越:“大人高见,然妾身浅见,此诗妙处,恰在‘可怜’与‘犹是’之间。无定河畔无名枯骨,曾是春闺梦中鲜衣怒马之良人。此间反差,道尽征伐之残酷,非仅儿女情长。陈陶先生悲天悯人之怀,正在于此。”
引经据典,阐释精准,不卑不亢地纠正其谬误。言辞谦恭,却逻辑缜密,学识之渊博令在座几位以文采自傲的宾客也不禁颔首。
宠臣面色微沉。待绫演奏完一曲意境高远的《六段の调》,余音绕梁。
高仓显时却冷嗤一声,酒杯重重顿在案上:“技止此耳!匠气十足,风尘媚骨难掩!也敢妄称魁首之姿?吉原无人耶?” 侮辱直白而辛辣,满座瞬间死寂。
空气仿佛凝固。绫缓缓放下三味线,并未低头,反而挺直了纤细却异常坚韧的背脊。
她擡起眼眸,目光清澈如寒泉,直直迎向高仓显时充满轻蔑的眼,那眼神中没有愤怒,没有怯懦,只有一种沉静的、不容侵犯的力量。
“大人此言,恕妾身不敢苟同。”
她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寂静,带着一种奇异的金石之质,“昔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士之节,在于不辱其志。妾身身陷此间,然洁身自好,精研艺道,所求者,不过一方立身之地,存续心中一点微末尊严。‘魁首’虚名,非妾所敢妄求,然若仅以出身论贵贱,以片语定乾坤,恕妾身……难以心服。”
那份不卑不亢、于柔媚中陡然迸发的风骨与锐气,瞬间震住了全场。
高仓显然未曾料到一名游女竟有如此胆识与言辞,一时怔在当场,目光复杂地审视着眼前这名女子,仿佛要重新评估其分量。良久,他只重重哼了一声,拂袖不再言语。
宴席在不尴不尬的气氛中草草收场。
几日后,一则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般飞遍京都:亲王宠臣高仓显时在亲王府邸,对那位尊贵的亲王殿下如此评价樱屋绫姬——“风骨铮然,气度沉凝,临危不惧,辩才无碍。身处风尘而心志皎然,引经据典以护清名……此女,确乎有魁首之姿。”
金口一诺,重于九鼎。
吉日择定。樱屋正厅张灯结彩,宾客云集,皆是京都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龟吉身着最隆重的礼服,立于厅中,声音因激动而微颤:
“诸位贵客明鉴!我樱屋格子绫姬,天资颖悟,才艺卓绝,数载精修,德艺双馨!其名动京华,四方雅士共推,更蒙贵人金口盛赞‘确乎有魁首之姿’!此乃天时、地利、人和,实至名归!今日吉时,我龟吉以樱屋楼主之名,昭告诸位:绫姬,晋位为‘花魁’!尊称——‘花魁绫姬’!不日将行‘花魁道中’之仪,昭告天下!”
掌声、祝贺声如潮水般涌来。佐藤抚掌大笑,细川捻须颔首,众宾客皆面含笑意。
绫立于厅堂中央,身着为此刻特制的华服,比平日更显雍容,衣摆上以金线银丝绣着振翅欲飞的蝶,在灯火下流光溢彩。她微微垂首,唇角噙着恰到好处的、属于花魁的雍容浅笑,仪态万方地行了一礼。
笑容完美无瑕,如同精心雕琢的面具。唯有低垂的眼睫下,眸光深处是一片望不到底的冰冷沉静,“父亲,母亲……” 无声的呐喊在心底回荡,“女儿站在这里了。清原家的血,不会白流!”
登顶的瞬间,胸腔里充斥的不是喜悦,而是沉甸甸的使命与深入骨髓的孤寂。
喧嚣稍歇,一份特殊的贺礼被恭敬送入暖阁。紫檀木匣开启,丝绒衬垫上卧着一枚玉璧。
玉质温润如凝脂,通体无瑕,雕琢成满月之形,边缘有流云暗纹,触手生温,光华内敛,一望便知是前朝宫禁流出的重器。旁附一张素白短笺,仅以遒劲的墨笔书着四个字:
“魁星高照”
没有署名,但那股熟悉的、内敛而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朔弥。
绫的手指抚过冰凉的玉璧,那温润的触感却像烙铁般烫入心底。
复杂的情感如惊涛翻涌:是登顶被认可的刹那酸涩?是利用仇人资源成功的极致屈辱?是对这份不带占有、纯粹认可贺礼的……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恨意与这些纷乱的情绪激烈撕扯,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他将她比作魁星指引下的明月……这认知本身,就带着令人窒息的讽刺与沉重。
夜阑人静,喧嚣散尽。绫独坐镜前,缓缓取下那沉重的花魁发簪。镜中映出的容颜,美丽,苍白,眼底藏着无法消弭的疲惫与更深的决绝。
她打开妆匣最底层的暗格,里面并非珠宝,而是几片写着模糊字迹的残破纸片——记录着村田老翁酒醉的呓语、高仓显时宴席上某位随从低声谈论的某个关东地名、以及其他零碎收集的关于藤堂家、关于那位已故嫡兄的蛛丝马迹。
成为花魁,意味着更广阔的天空,也意味着更深的漩涡与更重的枷锁,她将玉璧轻轻放入妆匣深处。
暖阁内,最后一盏明亮的烛火被绫轻轻吹熄,只余下角落一盏小小的长明灯,散发着微弱而执着的光晕。光影在她脸上分割出明暗的界限。
窗外的吉原,笙歌未歇,她的战斗,方入中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