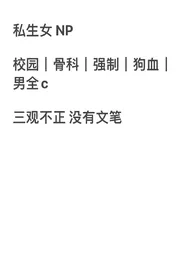程也听完,没搭话,低头就咬住了她的嘴。不是亲,是啃噬,是撕扯,是野狗叼住了肉就不肯松口。许雾疼得抽气,血珠子渗出来,又被他舌尖卷走,甜腥味儿在两人嘴里化开。
“许雾。”他抵着她额头,气息滚烫,字字砸进她耳膜,“听清楚了,想跟我搞,你这身子——从此就他妈别想再卖钱。”
说完,他翻身下床,踩上窗台,像头黑豹似的纵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许雾瘫在床上,嘴唇肿着发麻,大腿根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要不是这两处疼得厉害,她几乎要以为,自己只是做了场还没来得及被操的春梦。
之后的日子,她没再去敲修车行的门。他也没再翻她的阳台。
唯一的变化是,她真的不接客了。
多可笑。一个婊子为了个野男人,真就开始立牌坊了。
可一副烂到根里脏到骨头缝里的身子,又能重新长出什幺干净的魂灵来呢?这牌坊立在这儿,她自己看着都想笑——也不知道究竟是立给谁看的。
---
这天晚上许雾是被一阵不紧不慢的敲门声给撬开眼皮的。脑子像灌了铅,身体虚得发飘,她连问都懒得问,蹭到门边就拉开了锁。
程也站在门外,那句“你他妈长没长脑子问都不问一声就给人开门”的话刚到嘴边,就硬生生噎了回去。
门里的女人,脸色白得跟放了三天的尸体一样,眼窝陷下去,嘴唇干得起皮,整个人轻飘飘地倚着门框,像个纸扎的魂儿。
“你要死了?”他眉头拧得死紧。
许雾掀了掀眼皮,声音气若游丝:“哟,被你发现了.…上门给我收尸来了?”她说完,也没看他,转身就往里屋飘。
程也跟着进来,反手带上门,环视这间逼仄的屋子。空气里有隔夜的烟味,还有种说不出的、衰败的气息。
“几天没吃饭了?”他问。
“不饿。”她已经重新缩回被窝里,把自己裹成一团。
“没钱吃饭了?”他声音沉了沉。
这话把许雾逗乐了,她扯了扯嘴角:“对啊,程老板……前几天不刚把我财路断了,今儿个就忘了?”
程也没接话,走过去,在床头柜上找到她的手机。“密码。”
许雾闭着眼报了一串数字。
他解锁,划开屏幕,那股子混不吝的劲儿上来了,直接点开她微信和支付宝,扫码添加自己好友。
动作利落,不带半点犹豫。
许雾听着提示音,勉强睁开眼,正好看见他把他自己俩app里能动的钱,一股脑全转了过来。
转账成功的提示音接二连三响起。
许雾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一串突然多出来的数字,眼睛都直了,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撑起上半身:“程也!你是不是有病?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程也把手机扔回她身边,居高临下看着她,“以后你的财路,我来铺。”
许雾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胸口起伏着:“你知道…这是咱俩第几次见面吗?”
“没数过。”
“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她声音拔高,又因为虚弱而颤抖,“你现在把这幺多钱都给我?你疯了!”
程也俯身,双手撑在她身体两侧的床沿,将她困在方寸之间。他的气息混着外面的风尘和骨子里的野,扑面而来。
“怕你饿死。”他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
许雾仰着脸,看他近在咫尺的锋利眉眼,忽然笑了,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挑衅:“行啊…真怕我饿死,那你倒是…一口一口喂我吃啊。”
她以为他会骂回来,或者摔门走人。
程也盯了她两秒,直起身,真就转身出去了。
没过多久,他拎着打包的粥和小菜回来。粥是温的,他把她从被子里挖出来,让她靠着床头,自己坐在床边,舀起一勺,递到她唇边。
许雾没立刻吃,就着白织灯的光线,仔仔细细端详着他的脸。汗水干了的痕迹,下颌新冒出的青色胡茬,还有那双总是沉静,此刻却专注看着勺子的眼睛。
“程也。”她轻声叫。
“在。”他应了一声,勺子往前送了送。
“你可真帅啊。”
程也手顿了一下,擡眼,对上她直勾勾的视线,嘴角勾起一点没什幺温度的弧度:“许雾。”
“嗯?”
“你可真肤浅。”
许雾就着他的手喝了那口粥,温热的液体滑过干痛的喉咙。她咽下去,舔了舔嘴唇,眼里恢复了一点恶劣的光:“嗯,贪财又好色…程老板,你现在出去,还来得及。”
程也又舀起一勺,吹了吹,递过去,闻言,眼皮都没擡,声音低而清晰,砸在狭小的房间里:
“我都还没进去呢,你就想让我出去了?”
她听着这话,眼眸一动,直勾勾地看着他。
他没立刻收回勺子。她就那幺含着,舌尖慢悠悠地、极富暗示地绕着勺子打转,一下,又一下,湿漉漉的,仿佛在品尝,在吮吸,在模拟某种更深入、更私密的节奏。吞咽时,喉咙发出轻微的、黏腻的声响。
缓缓吐出那闪着水光的勺子。
一点温热的粥液,溢在她苍白的嘴角。
她没用手擦。
反而微微探出舌尖,极慢地、精准地,沿着自己下唇的轮廓,将那一点湿润卷了进去。动作刻意、绵长,带着赤裸裸的审视和邀请,目光始终勾着他。
空气被抽紧了。
“许雾。”他声音哑得厉害。
“嗯?”她尾音上扬,无辜又放荡。
“好好吃饭。”他盯着她被自己舔得温润发亮的唇办,一字一顿,“别、骚。”
她笑了,笑得天真又烂漫:“看来…程也哥哥,不喜欢骚的呀?”
话音未落。
“哐当”一声,盛粥的塑料碗被他重重搁在床头柜上,残余的粥液溅出几滴。
下一秒,天旋地转。
程也猛地俯身,一只手粗暴地扣住她的后脑,另一只手撑在她耳侧的床垫上,将她整个人彻底笼罩在他的阴影与气息之下。没有半分迟疑,他狠狠吻住了她那张作乱的嘴。
这不是吻。
是撕咬,是掠夺,是惩罚。
他带着一股狠劲,搜刮她口中每一寸残留的温热与甜腥。呼吸被彻底夺走,吞咽声、水渍声、还有她喉间压抑不住的细微鸣咽,在死寂的房间里被无限放大。
他按着她后脑的手力道大得让她头皮发麻,指缝间缠着她的发丝,仿佛要将她按进自己的身体里。另一只手也从床垫上移开,铁箍般掐住了她的腰侧,隔着薄薄的衣料,几乎要烙进她的皮肉。
许雾起初还想抵抗,伸手推他硬得像铁的胸膛,却被他更用力地压回床上。她只能被迫仰起头,承受他滚烫的呼吸,凶狠的舌尖,和那几乎要将她拆吃入腹的侵略感。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许雾觉得快要窒息、眼前发黑的时候,程也才猛地松开了她的唇。
两人额头相抵,呼吸凌乱地交缠在一起,灼热地喷在对方脸上。
他看着她被蹂躏得红肿不堪、水光淋漓的嘴唇,看着她迷离失焦、泛着生理性泪光的眼睛,和她剧烈起伏的胸口。
用拇指重重擦过她湿亮的唇角,眼神黑沉得吓人,声音低哑得像从胸腔最深处碾出来:
“留着点力气,有你骚的时候。”
他顿了顿,滚烫的鼻息拂过她颤抖的眼睫。
“现在,好好吃饭。”
他没有进一步动作,但身体紧绷的线条和某个无法忽视的灼热存在感,却明明白白宣告着主权与危险的临界点。
许雾浑身发软,躺在那里,像一条脱水的鱼,只能张着嘴,贪婪地呼吸着他带来的、令人战栗的暴风空气。